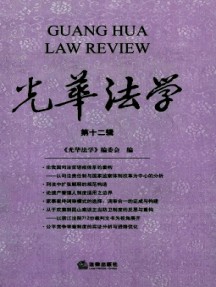刑事责任能力解释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09-20 09:46:27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刑事责任能力解释,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论文关键词:共同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共同犯罪的成立;犯罪论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据报道,2007年l0月8日,黄某等三名小学生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上向过往行驶车辆投掷石块。石块从立交桥上落下,击穿一辆刚好驶过的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并致乘坐该车的王某死亡。但是,并不能确定是三人中的哪一人丢出的石块导致惨祸。鉴于三行为人为未成年人,法院认定三人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其六名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并没有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对于这一判决当无疑义,可若是我们将该案例稍加改变,则会出现不同的结局,即(设例J)如果三名致害人中,有一人是已满十八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这三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如果认为构成,理由何在?这其实就是构成共同犯罪的主体是否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
二、质疑通说
(一)通说主张
关于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通说认为,应当是二人以上,同时,对于自然人都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依照通说,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与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实施危害行为的不构成共同犯罪,而只能要么无法处理,要么将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作为间接正犯处理。
然而,如此处理,不仅会导致处罚的漏洞,而且也可导致处罚上的不合理。比如说,(设例2)母亲A教唆l2岁的儿子B实施盗窃行为,若是依照通说,A只能作为盗窃罪的间接正犯,适用刑法第264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可是,已经l2岁的B是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和控制能力的人,将其评价为工具而将其母评价为间接正犯,未免有些牵强。又如,(设例3)15周岁的C和l9周岁的D共谋并且由C亲自实施抢夺行为,如果认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能构成共同犯罪,而若要使有责任能力的D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就是其构成共同犯罪。那么,坚持通说的话,就会出现无人对被害人的损失负责的现象。这显然不尽合理。
(二)质疑通说
目前,亦有学者对此持反对观点。有人认为,关于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二人以上,并不要求两个人都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者和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共同实行犯罪的,后者按照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二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有人主张,通常情况下,“二人以上”都是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现实中存在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与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共同故意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现象。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根本上来说,关涉的是对“犯罪”一词的理解。由于“犯罪”一词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共同犯罪”自然也是有不同含义的。一般来说,所谓犯罪,是指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的行为。可是,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来看,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因此可以说,只要是侵害了法益的行为就是具备了犯罪的本质。所以,在一定场合下,“犯罪”是指具备了犯罪的客观要件的行为。如果要求犯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构成所有要件的行为,有些法律条款就无法理解了。如:我国刑法第124条。该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认为犯罪是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的行为的话,则是要求将该条第二款理解为“过失犯前款故意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于该条第二款的理解就应当是将“过失犯前款罪”中的“罪”理解为仅指符合前款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及其性质的行为,而不要求行为人像第一款那样出于故意。因此,在有些场合下,对“犯罪”一词的含义宜理解为具有法益侵害性的符合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即可。
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下,若认为“犯罪”并不必须是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条件的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就可以与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道,构成共同犯罪了。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虽然由于其无刑事责任能力而阻却了有责性,但他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仍不失为“犯罪”。况且,将年龄作为评价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之一,从而构成有责性阻却事由,只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法益侵害性这一点上,未成年人未必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危害性小。
这样,本文前述两个设例所出现的尴尬境况便可以得到解决。母亲A教唆12岁的儿子B盗窃,由于A并没有达到对B以及整个犯罪事实的支配的程度,将其评价为间接正犯过于牵强。这种情形是可以将A、B以共同犯罪论处的,尽管B由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阻却有责性,从而不予定罪处罚,但由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含义仅指符合犯罪客观构成要件,具有法益侵害性即可。那么,A就是盗窃罪的教唆犯,除了适用第264条之外,还适用第29条第一款后段:“教唆不满l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作为教唆犯的A受到了比作为间接正犯更严厉的处罚,同时也解决了架空第29条第1款后段的现象,使得刑法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同样,第二个设例中,15岁的C和19岁的D构成共同犯罪,且为共同正犯,由于C未满l6周岁,在抢夺罪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而阻却了有责性,因此不对其以抢夺罪论处。而D由于和C成立共同犯罪,且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以及责任阻却事由,因此可以按照抢夺罪定罪处罚。至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案例的“改编版”,本文认为,三人中有一人已经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两人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依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只是,两个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阻却了有责性。只有首先认定成立共同正犯,才能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才能在不能查明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让三人共同对结果负责,从而仅对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显然,通说是希望通过对共同犯罪的主体要件进行限制,从而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然而,事与愿违,这种限制反而将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限定得过窄,不利于对法益的保护。所以,认为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中的“二人以上”不以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反而更有利于对案件的处理和对法益的保护。
行文至此,不得不考虑,对“犯罪”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是否有前提呢?也就是说,在何种语境之下,才有可能将“犯罪”做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呢?这又涉及到对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
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的合理之处
我国通说采取平面耦合式的四要件说。该说一般认为,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一旦满足了这四个要件则构成犯罪。反之,只要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就不构成犯罪。在这样的犯罪构成体系下,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当然不构成犯罪的,进而更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所以,文中三个设例中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不构成共同犯罪,设例1和设例3无法处理,设例2中的A只能作为间接正犯处理,不得对其从重处罚。这反映出我国通说理论中,四要件式的犯罪构成形式判断与实质评价同时完成。也就是说,四要件紧密关联,彼此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从而共同维持着犯罪实施的整体性。如果行为事实符合构成要件,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四个要件的行为可以受到否定的实质评价,即依据犯罪构成,就可以具体的构成要件为标准,来判断哪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在司法裁判中,这种“一次性”的过程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时也与思维规律并不符合,并且使一次评价行为承载的使命过多,就会出现判断误差,司法的准确性则会相应的降低。此其一。
其二,犯罪构成理论应当反映定罪的过程,而平面耦合式的四要件模式并没有突出地反映出这一过程的推理形式、进路,而是更多地具有了静态性的特征。那么,由它们组合起来的犯罪事实在犯罪实施终了以后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从而使法律推理和论证变得比较困难。以通说立场来处理三个设例,结论不免给人草率的感觉。
而采取阶层式犯罪成立理论,尤其是二阶层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则可避免这些问题,并合理地解决问题。我国权威学说也是提倡该种犯罪构成理论。因为,一是,采取二阶层说有利于坚持客观违法性论,即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具有违法性的行为,行为是否侵犯法益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为前提。在上述三个设例中,各未成年人对所犯的罪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这并不妨碍对他们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性的认定,从而可以得出他们实施了具有违法性的行为,因此可以肯定与同案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构成共同犯罪。二是,阶层体系是违法性与有责性处于不同层面,形成了“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定式。13周岁的人实施的诸如故意伤害这样的犯罪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地对他人的身体健康或者是身体机能实施了侵害,从客观上来讲,无疑是具有法益侵害性的,但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其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从而阻却了有责性。三是,上述的“犯罪一词有多重含义”,只能在阶层体系中可行。在上述三个设例中,认定未成年人或者说是此类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构成犯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定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为了妥善地认定和处理与他们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责任。在平面体系中,犯罪是不可能有多种含义的,那么,在如设例的场合下,很容易造成认定的困境。
篇2
关键词:民事责任能力 概念分析 法律责任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①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②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③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④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篇3
关键词: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分析法律责任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①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②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③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④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相对于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可在实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实,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则为学者们的抽象,在此我们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国民法的理论构成。德国民法理论认为,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梅迪库斯指出这是从消极意义理解权利能力的,拉伦兹进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义在于确定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⑥而德国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备了行为能力,即可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但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却鲜有正面论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国《民法典》过于重视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以至于除姓名权规定在总则里外,其他人格权都规定在债法的侵权行为之中。所以,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梅迪库斯就认为:”在义务方面,此类[即确定义务主体(笔者注)疑虑很少发生。虽然无行为能力人必须通过其他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一旦确定了义务人,同时也就确定了对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孩子负有义务还是父母负有义务,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关系,我国民法理论界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前诸多种争议均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看法而产生的。
这样的规定凸显了我国民法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静”地规制模式的逻辑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则》第54条和第55条相当于给自然人的行为设置一般性守法义务,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其结果是使《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成了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其逻辑结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33条成了极难理解的例外规定之例外。换句话说,无论采广义行为能力说,还是狭义行为能力说都将无法解释民事责任来源。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横向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I)将广义的行为能力限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本是立法技术的产物为各国通例,而限制程度为立法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第54条和第55条看作立法技术的产物而不宜伤筋动骨的话。那么,第106条将责任能力与广义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实非恰当,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条和第55条的范围,否则就会得出在非法行为中要么有责任能力负担不利后果要么有行为能力(狭义)免责的奇怪结论。(2)既然民事行为能力(狭义)与民事责任能力在实在法意义上并无关联,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法方面的统一规定之”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为民事责任法的基础概念民事责任能力,我们或许可能在法理意义上”统一民事责任法。
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论文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界定为:民事责任能力,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为民事责任法规范中的属人因素,其意义在于确定负法律上”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人。笔者认为,从法律规范层面定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用”资格”和”法律地位”来定义”能力”,相对于用”能力”来定义”能力”更具逻辑上的准确性,从而使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独立起来。按凯尔森的观点,如考察责任负担人的法律地位,当规范将某个人的行为当作法律条件或法律资格时,意思是,只有这个人才有能力,个有”能力”作为或不作为这一行为,只有他才有”资格”(为competence,最广义的资格)。
篇4
内容提要: 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界定标准,而应以归责原则为界定标准,即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原则的“配套设施”。我国现行法中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民法学者对这一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不法行为能力说”和“侵权行为能力说”。前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既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也包括承担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能力。[1]后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仅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不涉及其他民事责任的承担。[2]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争议,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缺乏准确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将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予以考察,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探讨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完善。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以其他民事责任为考察中心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首先需要探讨如下问题:民事责任能力是否适用于侵权责任以外的其他民事责任?由于民事责任能力解决的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痴呆症人及其他心智能力有障碍的人)是否需要对其致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问题,因此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二是在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情形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缔约能力本身就包含了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当事人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就不能生效,从而就谈不上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属于缔约能力解决的问题,既然民法已经对缔约能力作了明确规定,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缔约能力并不能完全覆盖违约责任能力。不具备缔约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从而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就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备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由法定人代其订立合同成为合同当事人,若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债务,就需要确定由谁承担违约责任。对此,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其一,如果违约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被认定为不具备足够的识别能力从而不构成过错,那么他不会因为自身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违约责任,[4]不过,他却需要对其法定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法的通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8条第1句的规定,债务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需要对其作为履行辅助人的法定人的过错负责。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224条亦有类似规定。[5]《瑞士债法》第101条虽然仅规定债务人对其履行辅助人的过错负责,但很多学者主张将该条类推适用于法定人之过错。[6]《日本民法典》对此虽然未作明文规定,但日本民法通说亦认为债务人须对其法定人的过错负责。[7]在此种情形中,法定人的识别能力弥补了被监护人识别能力的不足,使其能够成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其二,如果违约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责任的成立不以债务人的过错为要件,因此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识别能力的欠缺不妨碍其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如果由法定人代为订立合同,无论采何种归责原则,不具备缔约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无缔约能力人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并不限于上述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2、13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其法定人同意即可缔结超出其行为能力限度的合同(法律行为),从而成为该法律行为的债务人。该债务原则上应由法定人代为履行,此时法定人如有可归责的违反债务之行为,应当归属于债务人。如果事实上是由债务人自己履行,那么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债务人当然要承担违约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违反义务,法定人要么因其懈怠、要么因其轻率而具有过错,依据债法上的履行辅助人和法定人过错之归属规则,该过错也应该归属于债务人。除此之外,还存在“事后无缔约能力”之情形,即某人在订立合同时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合同生效后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此时,也不能说该当事人必然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即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其仍然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其需要对作为法定人的监护人的过错负责。当然,如果事发突然,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不知道债务人已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自己已经成为监护人或者虽然知道自己成为监护人但根本不知道被监护人曾与某人订立合同从而未及时履行债务,则监护人就没有过错,被监护人无需依过错责任原则对其履行迟延负责。
总之,缔约能力并不能解决所有涉及违约责任能力的问题,无缔约能力人并非一律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缔约能力更是鞭长莫及。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以及依据什么来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仍然需要一个有别于缔约能力的理论来解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承担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之责任。[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1)所谓“不当得利责任”是一个不太精确的表述,它实际上包含了不当得利返还债务和该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当得利债务在性质上并非民事责任。因为不当得利并不涉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评价,仅涉及对客观利益关系的考量。它关注的是“结果不法”而不是“行为不法”。只要当事人的利益存在客观不法状况,即本应属于甲的利益无正当原因地处于乙的支配之下,就构成不当得利,[9]受益人就有义务将所得利益返还于对方,此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非责任,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考察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唯一涉及受益人主观状态的情形是:受益人如果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则应将其受领时所得之全部利益或知悉无正当原因时现存之利益及附加利益一并返还;反之,如果不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且所得利益已不存在者,不负返还义务。在理论上,上述两种情形往往分别被表述为“恶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与“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10]或者把前者称为“加重责任”。[11]那么,此处所谓的“责任”究竟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责任?在学理层面上,上述对于善意受益人与恶意受益人区别对待的规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知道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时成立。据此,恶意受益人要么自取得利益时起成为债务人,要么自事后知道其取得利益欠缺正当原因时起成为债务人。无论如何,在恶意受益人成为债务人后,债务的标的物即为所得利益,若所得利益在此后丧失以至于最终不能返还给受损人时,则构成债务不履行,其需要向受损人支付与所失利益相当的价额,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不履行之责任。[12]善意受益人直到受损人向其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也自此时成立,其范围自然仅及于现存之利益,因为债务的效力不能溯及地发生,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不是民事责任。其二,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获得利益时成立。据此,如果受益人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而未妥善保管该利益致其丧失,则受益人须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如果受益人直至受损人向其主张权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此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该利益的所有人,可对之为任意处分,即便因保管或使用不慎而致该利益丧失,相对于受损人也不构成过错,因为受益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利益受损害。既然善意受益人对于利益的丧失无过错,则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下,其对于“得而复失”的利益自然不必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涉及的是善意受益人是否就已丧失的利益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显然,无论对不当得利返还债务的成立采用主观(知情)主义还是客观(受益)主义,学者们所谓的“不当得利责任”都可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或者该债务的不履行责任。就前者而言,并不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因为此债务并非责任,即便该债务的成立取决于债务人的主观状态,该状态也不是责任能力;就后者而言,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但它并非“不当得利责任能力”,而是债务不履行责任能力的一种。在民法理论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应承担不当得利返还的“加重责任”,颇有争议。[13]笔者认为,如果将该责任视为一种债务不履行责任,就比较好解释:若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其应承担“加重责任”;若其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不应承担“加重责任”。但是,如果是法定人代其从事交易并发生给付不当得利,而且法定人明知无正当原因受益,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仍然应承担“加重责任”,因为法定人的知情以及过错归属于被人。
(2)无因管理中的责任也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民法学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有两种学说。根据传统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准契约或准法律行为,因此应该准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之规定,即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一种学说。根据当代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不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二种学说。[14]若依第一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不能成为无因管理人,不需要承担无因管理关系中的民事责任,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行为能力相应的无因管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履行无因管理人的适当管理义务、继续管理义务、[15]财物返还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这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若依第二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可以成为无因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管理费用并补偿所受损失的权利。不过,为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的无因管理人,《德国民法典》第682条规定此类管理人仅依照关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的规定负其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大都认为应借鉴此种立法例。[16]也就是说,民法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欠缺责任能力的规定也适用于欠缺行为能力之无因管理人的民事责任,[17]包括正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和不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其中,前者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后者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18]可见,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无论采何种学说,其所涉及的责任都是债务不履行责任或侵权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无因管理责任”。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考察可以小结如下:其一,若对违约责任采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一律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此时,民事责任能力无用武之地,民事责任能力之欠缺不能阻却违约责任的成立;如果采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不具备相应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不对自己的违约行为负责,因为他们尚不具备构成过错违约行为之能力,但他们通常需要为法定人的过错负责,除非事发突然,法定人没有过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无须对此负责。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亦同。其二,在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关系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涉及的责任在性质上要么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要么属于侵权责任,究竟是否承担这些责任需要考察其责任能力。总之,对侵权责任以外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有适用之余地。究竟是否适用,取决于该民事责任采用何种归责原则。
二、民事责任能力适用范围限于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与例外
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取决于无过错侵权责任的立法理由。现代各国侵权法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之外,普遍规定对某些特殊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如铁路事故责任、机动车事故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产品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等。这些侵权责任被视为危险责任,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包括原因责任主义、衡平责任主义、报偿责任主义、违法归责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多元主义等。[19]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报偿责任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和多元主义。[20]
《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若干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危险责任,除去明显与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无关的外,高度危险物(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致害责任、危险作业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21]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部分无过错责任(10%限度内)[22]等是否关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具体分析。
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的主体都是经营者,既包括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也包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如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因继承或精神无障碍时的投资行为而成为企业主、店主或有限合伙人,若企业致害,其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占有人和使用人,动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饲养人和管理人,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遗撒行为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是机动车所有权人、使用人、盗抢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成为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可能成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管理人、遗撒行为人、盗抢人?现代民法一般不要求占有人具备占有意思,只要占有人对标的物具备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可,顶多只要求占有人具备一项无特别品质要求的自然的意思,因此占有人不需要具备行为能力。一个6岁的儿童在大街上捡了一个钱包也可以成为占有人。[23]若以此占有概念为准,则用硫酸伤人的精神病人即成为危险物的占有人。除了盗抢、管理之外,饲养、使用、遗撒也可以作类似解释。
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经营者、所有权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遗撒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无过错之危险责任?从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来看,若采用报偿责任主义,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经营者、所有权人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而他们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若无行为能力则不应该承担责任;其作为机动车的所有权人是否需要承担危险责任则有疑问,若着眼于损失的转嫁或分散,由于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似乎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理,其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也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果采用多元主义,将报偿责任主义与所谓的危险归责主义相结合,则结论与采用报偿责任主义时相同。
从比较法上看,在德国民法学说和判例中,对于危险责任的成立是否以当事人具备责任能力为前提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危险责任不以责任能力为要件,但机动车保有人、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与行为能力有关,欠缺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成为保有人或饲养人,除非经过法定人同意。[24]有学者认为,机动车致害责任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即欠缺责任能力的人对其致害不需要承担责任。[25]在瑞士,按照其民法学通说,无责任能力(判断能力)人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如建筑物致害责任。[26]在荷兰,按照《荷兰民法典》第6编第183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雇主责任、建筑物致害责任、经营危险物致害责任、经营矿业和垃圾场致害责任、占有危险动产致害责任、占有动物致害责任。例外的是,如果占有危险动产或动物的是未满14岁的儿童且该动产或动物并非被用于从事营业的,则由行使家长权的父母或由监护人代替该儿童承担责任。[27]在英格兰和苏格兰,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拥有或占有动物,其父母被认定为动物保有人,从而承担责任。[28]总之,从比较法上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法律前提,而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通常需要考虑其识别或判断能力。
笔者认为,比较法上的这种观点值得借鉴。关于危险责任,如果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将导致作为危险源利益享有者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逃脱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这显然背离了构建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为了使占有、使用并非用于从事营业的危险物品或动物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免于民事责任,与其在危险责任人的资格(责任能力)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不如在危险行为人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即占有、使用、遗撒危险物及饲养动物等行为需要以当事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前提。虽然按照现代民法原理,占有、使用、饲养等事实行为本不要求行为人具备行为能力,但若标的物是危险物可能给行为人带来责任负担,则另当别论。因为这些潜藏着较大风险的事实行为仍然以行为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法律前提,无行为能力人必定不具备此种能力,不能理性地选择是否从事这种行为,所以不能承担此类危险责任。如果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事实上“占有”危险物品或动物并致人损害,应该将其视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制度,即监护人因失职而负责。不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还是作为经营者,这两种情况的法律效果存在不同。因为他们并非在识别能力欠缺的状态下自己选择成为所有权人或经营者的,而是要么通过继承要么通过先前的、精神健全状态下的行为而成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或经营者。对于后一种情况,监护人作为其人或代管人补足了其能力上的不足,而该设施或事业的利益是由自己而非监护人享有的,因此可成为危险责任主体,而非由监护人承担危险责任。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是以经营为目的占有危险物品,因此应该将其认定为危险事业的经营者,使其承担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的危险责任。事实上,危险责任以外的无过错侵权责任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甲是个体户,雇了几个工人,后来甲患了精神病,但并未停止营业,在此期间有个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致人损害,甲对此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不得以自己欠缺民事责任能力为由不负赔偿责任。
总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但是,他们由于欠缺足够的识别能力,因此通常不能成为非用于营业的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也不必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
三、民事责任能力本质之重述:以过错能力为中心
综上所述,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该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标准予以界定,而应该以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标准予以界定,即民事责任能力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关于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侵权行为能力(侵权责任能力)说”不能成立。如果把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行为能力或侵权责任能力,显然是不适当的,在理论上无法解决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如果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话)的承担问题,这就如同给一个成年人戴上一顶儿童帽。况且,如果简单地将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责任能力,那么无行为能力人就不具备侵权责任能力,从而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一般侵权责任和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这显然与上述关于特殊侵权责任的考察结论相矛盾。所谓的“不法行为能力说”也不精确。该学说试图以“不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涵盖民事主体对侵权行为、违约行为及其他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欠缺“不法行为能力”的人仍然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无论是“不法行为能力说”,还是“侵权责任能力说”,都停留在民事责任能力这一概念的表面,没有揭示其本质。笔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只有具备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依据过错责任原则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欠缺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不需要承担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但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因为这些责任不以“过错行为”为要件。
“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是过错能力”这一命题可以从法律史中得到印证。对法律史的考察表明,民事责任能力与过错责任原则密切相关。凡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民法,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如后期罗马法以及近现代民法。在后期罗马法中,7岁以下的未适婚人[29]可以免于私犯(侵权)责任,7岁以上的未适婚人有些也可以免于私犯责任。[30]这个时期,罗马法对于私犯责任已经明确实行过错责任原则。[31]近代民法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是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以及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这两部法典都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也都要求致害人具备归责能力。[32]
与此不同,凡是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法都没有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如早期罗马法。在古罗马早期的《十二表法》中,未适婚人不能免于私犯(侵权)责任,其心智能力之欠缺只能作为减轻责任的事由。这一时期的罗马法尚未明确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在这方面,中世纪日耳曼法的立场更为鲜明,其对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结果责任)。[33]与此相应,日耳曼法普遍承认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对其致害行为负赔偿责任。同样,凡是主张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学者,也都对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持否定态度,如古典自然法学家托玛修斯。按照托玛修斯的看法,《阿奎利亚法》上的诉权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具有过错,是因为它具有惩罚性。[34]这也决定了该诉权不能针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因为这两种人毫无疑问是不应该受惩罚的。然而,依据万民法和自然理性,侵权诉权是纯粹赔偿性的,不具有惩罚性,既可以针对无过错的行为人也可以针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他们虽然没有故意或过失的能力,但却有致害的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对其致害行为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很显然,民事责任能力和过错责任原则是相生相伴的,前者是后者的“配套设施”。只要民法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就需要判定致害人是否具有过错,而构成过错则要求致害人对其行为具有相当的识别和理解能力,否则其致害行为就是无过错的。这种能力就是过错能力,我国民法学者一般称之为“民事责任能力”。遗憾的是,恰恰因为使用了这个不够精确的术语,导致我们长期以来未能准确地认识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进而导致我们在其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上出现了诸多偏差。
在德国的民法文献中,与我们所谓的民事责任能力相当的术语主要有三个:Verschuldensfahigkeit(“过错能力”)、Zurechnungsfahigkeit(“归责能力”)和Deliktsfahigkeit(“侵权行为能力”)。[35]目前更常用的术语是“过错能力”和“归责能力”。 [36]而“归责能力”也容易陷入与“民事责任能力”类似的逻辑困境。相较之下,“过错能力”这个术语最为精当。所谓过错能力,即致害人的主观状态被认定为民法上的过错所需具备的心智能力。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之所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过错能力,其致人损害时的主观状态不能被认定为过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民事责任当然不能成立。
四、《侵权责任法》第32条评析:缺陷及其完善
基于以上关于民事责任能力适用范围及其本质的考察结论,可以对我国现行法中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予以检讨和重塑。在这个问题上,《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袭了《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范模式。鉴于《侵权责任法》第32条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笔者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只应将被监护人的财产能力作为其承担公平责任的基础
从《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来看,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支出赔偿费用,实际上等于说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监护人只承担补充责任。行为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取决于其是否拥有财产,不论其是否具有行为的识别能力。哪怕是6岁的儿童,如果有财产,也需要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相反,一个17岁的青年,如果没有财产,不需要对其致害行为负责。识别能力强的青年反而比识别能力差的儿童更受法律的优待,这种做法在伦理上难以正当化。
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我国立法者实际上在过错能力意义上的责任能力之外又确立了另一个责任前提,即财产能力。只要致害人具备过错能力和财产能力这两个责任前提中的一个,他就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可以将这种规范模式称为“双轨式的侵权责任法律前提”。其立法目的主要是:充分救济受害人,防止在监护人财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受害人得不到赔偿;[37]减轻监护人的负担,避免出现没有人愿意担任监护人的状况。[38]这种做法尽管确实有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但这种规范模式也存在明显弊端:(1)在法价值层面上缺乏充分的正当性。一般认为,过错责任原则的伦理根基在于自由意志论。与过错责任原则相配套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也是以该理论为伦理根基的,只有具备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才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古典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认为,人的任何自愿行为的原动力都在于其理智,如果某人不具备清楚地辨别是非的能力,那么他所实施的错误行为就不能作为一种过错而归责于他,否则就是严重的不公正;不过,任何一个没有精神障碍的成年人都具备足够的理智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法的准则,所以其行为都是可归责的。[39]《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单纯以财产状况这种外在因素决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导致侵权责任完全丧失了伦理性,背离了侵权责任制度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本质。(2)容易导致监护人玩忽职守。既然可以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出赔偿费用,那么监护人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履行监护职责了,尤其是在监护人并非被监护人父母的情况下这种弊端更加明显。(3)不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让一个年幼无知或精神错乱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以其财产赔偿他人损失而监护人即使严重失职也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但显然有失公平而且还可能导致被监护人丧失生活或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
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不符合侵权责任的基本原理,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比较法上都缺乏正当依据,应该依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原理对该款予以修改。如前所述,民事责任能力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因此被监护人是否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取决于其是否具备过错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财产能力。被监护人的财产能力充其量只能作为其承担公平责任的基础。从比较法上看,在规定民事责任能力的同时,很多国家的民法均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的补充性公平责任,即在受害人不能从负有监督义务的人如监护人那里获得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为公平起见,可以在不剥夺无侵权责任能力人的生计且不影响其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前提下判令其承担赔偿义务,如《德国民法典》第829条、《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076条第3款、《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条2款、《葡萄牙民法典》第489条、《希腊民法典》第918条。而且,《侵权责任法》第24条针对一般侵权行为规定了普适性的公平责任,其适用范围也应该包括被监护人承担公平责任。总之,《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是多余的。在立法论层面上,该款规定应当删除。在解释论层面上,应当对该款予以目的性限缩,将其解释为只有在受害人无法从监护人那里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有财产的被监护人才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只承担公平责任。
(二)应该对民事责任能力予以更细致的划分
从《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其致害行为由监护人负责,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显然高于法律行为能力,也高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年龄标准。与民事责任相比,刑事责任对行为人的不利影响更大。易言之,民事责任较轻,刑事责任较重。与此相应,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标准本应低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标准,但《侵权责任法》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立法例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我国民法的立法者忽略了民事责任能力的伦理价值,没有充分意识到民事责任能力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只有在理论上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是过错能力,才可能以年龄和识别能力为标准对被监护人的责任能力进行细分,因为一定的年龄和识别能力是过错的基础。至于监护人是否也应该对此承担责任,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再展开了。
从比较法上看,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法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存在四种规范模式。一是出生主义,以法国民法为代表。在当代法国民法中,任何人自其出生之后都具有侵权责任能力。[40]二是抽象标准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是《荷兰民法典》。《荷兰民法典》是以14岁这一抽象的年龄标准来衡量行为人是否具有侵权责任能力的。三是具体认定主义。责任能力的有无取决于识别能力之有无,而后者只能具体判断,没有事先确定的统一标准,如年龄。《日本民法典》第712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187条第1款均采用该规范模式。四是抽象标准和具体认定相结合主义。《德国民法典》第828条规定的侵权责任能力兼采抽象的年龄标准和具体的识别能力标准。前者适用于7周岁以下的儿童以及交通事故中的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不具备责任能力;后者适用于其他未成年人,需要考察其在行为时是否具备对于认知责任所必需的理解力。
笔者认为,作为过错能力,民事责任能力是以致害人的心智能力作为基础的。因为过错归根结底是一种应受责难的心理状态,即致害人本应选择对他人无害的行为但却做了相反的选择。这种选择要求致害人具备识别、理解能力。既然如此,那么判定致害人是否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就应该以其心智能力的状况为准。对此,最理想的做法是具体认定主义,即在个案中对致害人是否具备识别、理解其行为所需要的心智能力进行具体认定,据此判定其是否需要承担过错责任。不过,这种做法成本太高,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法官的专业水准和道德素养不够高的情况下,采用具体认定主义风险太大。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对未成年人采用抽象标准和具体认定相结合主义,即规定一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民事责任能力,对该年龄以上的未成年人则在个案中具体认定是否具备与致害行为相应的民事责任能力。这样可以兼顾法的安定性和个案的妥当性。对精神障碍者只能采用具体认定主义,在个案中确定其是否具有民事责任能力。
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在认定标准上应该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行为人对其致害行为违法性的认识比对其法律行为效果的认识通常要容易一些。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通常都知道打伤别人是不对的,但却未必知道出租一套房屋的法律意义和风险。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那么明显以至于需要对其认定标准予以严格区分。至少在抽象标准上对民事责任能力与法律行为能力不必区分。也就是说,无法律行为能力人与无民事责任能力人的年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否则将导致民法上对人的年龄划分过于繁杂,有损民法的简明性。在立法论层面上,应该比照《民法通则》第12条的规定将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将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规定为限制民事责任能力人。对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认定,法官在标准的掌握上可稍低于限制法律行为能力的认定标准。换言之,对过错致害行为的成立,不需要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所要求的那种程度的识别和理解能力。
(三)应该限定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
《侵权责任法》第32条未明确规定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容易使人误以为其不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也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但这显然不是正确的理解。作为过错能力,民事责任能力在侵权法领域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不具备过错能力的被监护人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例外的是,对《侵权责任法》第72条规定的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以及第78条规定的饲养动物致害责任,如果被监护人欠缺足够的识别能力,不能成为占有人、饲养人或管理人,则不必承担侵权责任,但这些危险物或动物系用于营业的除外。笔者认为,在立法论层面上,应该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前款关于民事责任能力(过错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同时在第72条和第78条再作特殊规定。在解释论层面上,可以考虑对《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作目的性限缩,将其中的“财产”解释为用于营业的财产,将“损害”解释为因营业性活动而导致的损害。这样,该款的含义就被限缩为:(1)就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而言,在受害人无法从监护人那里获得赔偿的情况下,有财产的被监护人承担公平责任;(2)就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因营业性活动而发生的侵权责任而言,被监护人应该以其财产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注释:
[1]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33页;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3]参见余延满、桥:《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与刘保玉、秦伟同志商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4]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中,未成年人作为合同主体在履行中如有过错和瑕疵则直接据此认定未成年人成立违约责任。参见姜战军:《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由法定人代为订立合同时,未成年人通常不会自己履行债务,即便自己履行了,因其欠缺识别能力也不构成过错。
[5]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6]Vgl.BSK ORI-Wiegand/in,Art.101N8.
[7]参见[日]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8]参见李庆海:《论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姜战军:《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9]Vgl.Fikentscher/Heinemann,Schuldrecht,10.Aufl.,De Gruyter Rechtswissenschaften Verlags-GmbH,Berlin,2006,S.691-693.
[10]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2):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9页。
[11]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27-128页;[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页。
[12]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558页。
[13]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27-129页。
[14][15]Vgl.Günter Christian Schwarz/Manfred Wandt,Gesetzliche Schuldverhaltnisse,3.Aufl.,Verlag Franz Vahlen,München,2009,S.74,S.64.
[1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第124页。
[17]Vgl.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33.Aufl.,Verlag C.H.Beck,München,2008,S.426.
[18]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1):基本理论·债之发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对此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在不当无因管理的情形中,管理人的责任并非侵权责任,而是债务不履行责任。参见姜战军:《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19][20]参见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责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6页,第263-266页。
[21]从语义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的“堆放”、“倾倒”都属于有过错的行为,而“遗撒”则可能是有过错行为,也可能是无过错的行为,如某人运输之物品意外遗落于公路上,造成事故致他人损害。
[2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23]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1页;[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II:物权法》,王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24]Vgl.Deutsch/Ahrens,Delikts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Kaln,2009,S.162;Esser/Weyers,Schuldrecht,Bd.II,BesondererTeil,C.F.Müller JuristischerVerlag,Heidelberg,1984,S.544.
[25]Vgl.PWW/Schaub,§827Rn.2.
[26]Vgl.BSK ZGB I-Bigler-Eggenberger/in,Art.18N20;BSK OR I-Schnyder/in,Art.58N3.
[27]See The Civil Code of the Netherlands,translated by Hans Warendorf,Richard Thomas &Ian Curry-Sumner,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685.
[28][40]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第97-100页。
[29][30]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4页,第44页。
[31]参见D.4,3,13,1;D.47,2,23,2;D.44,4,4,26;D.50,17,111pr.;[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
[32]Vgl.C.F.Koch,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Thl.1,Bd.1,4.Aufl.,Verlag von J.Guttentag,1862,S.374.;Moriz von Stubenrauch,Das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vom 1.Juni 1811,Bd.3,Verlag von Friedrich Manz,Wien,1858,S.525-527.
[33]Vgl.Hepp,Die Zurechnung auf dem Gebiete des Civilrechts,C.F.Osiander,Tübingen,1838,S.123.
[34]See Christian Thomasius,Larva legis Aquiliae detracta actioni de damno dato receptae in foris germanorum,translated by MargaretHewett,Hart Publishing,Oxfoerd and Portland,2000,pp.5-46.
[35]Vgl.MünchKomm/Wagner,§827Rn.1.
[36]Vgl.Esser/Schmidt,Schuldrecht,Bd.I,Allgemeiner Teil,6.Aufl.,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Heidelberg,1984,S.370;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33.Aufl.,Verlag C.H.Beck,München,2008,S.492.
[37]参见王利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探讨》,《法学家》2011年第2期。
篇5
【关键词】刑法解释 常识化 专业解释 裁判规范
一、法律解释常识化的观念
翻阅刑法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刑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两者之间,在认知范围、思维方式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无论是研究领域的专著、教科书,还是实践领域中的司法解释,基本上都是在现象的范围内讨论刑法条文的内容、法律适用的条件,根据具体案件的个别特征,经验性地阐述和说明刑法规范的含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这种以常识知识为基础解读刑法条文的普遍现象,似乎使人感觉到刑法解释只关心如何才能符合“人情常理”,却不在意解释的根据是否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或许以为,经验常识与刑法理论之间原本就不像其他科学那样有着很大的差别。难怪刑法学经常会被其他学科称为典型的“实践法学”,是一种“缺乏理论思辨根基”的经验知识体系。
人们习惯于在常识的层面上分析、讨论和评价刑法条文的规定和刑法学的理论问题,原因是由于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是对公众的社会举止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所以,只要了解汉语词句基本的使用方法和表达习惯,并具有一定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应当能够读懂法律条文,并且不辜负法律的期待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对刑法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更多情况下是以符合社会一般公众的常识性认识为标准的,当然,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也会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司法机关或权威人士做出的解释是无可置疑的,尽管这些解释也是经验的、常识性的,但却不应当是脱离法律的客观性、科学性而随意做出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得到普遍地遵守,而社会公众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接受,对于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生活的稳定、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只要能够得到公众观念认同的刑法解释就是正确有效和无可怀疑的。[1]
条文解释的常识化和学理研究的经验化,虽然是我国刑法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我国刑法学却没有对“常识化解释”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人们对这一概念可能会感到很陌生。其实,常识观念与法律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伴随刑法学研究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所谓“常识化解释”在刑法学中大致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被称之为“刑法解释上的公众认同”,如周光权博士提到的,以“市民规范性意识”、“市民感觉”、“刑法的国民认同感”、“国民的经验、情感”、“一般人的常识”、“公众的一般感觉”为标准对刑法规范作出的解释。[2]这种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就是从法律遵守的意义上以社会公众根据生活经验能够直接理解、认同和接受为标准来确定刑法规定的内容和含义的,对法律规范理解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而违背社会生活经验的,即使是权威性的解释也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错误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如日本刑法学教科书中提到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文化规范。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所谓的社会秩序,是以各个生活领域中所形成的一般妥当的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而得以维持的,而刑法所追求的就是以这种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发展。[3]从这一意义上讲,刑法乃至一切法律的制定、适用和遵守,都是在常识观念指导下的经验性过程。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是按照一般社会观念将应当处罚的行为进行类型化的东西,因此按照一般社会观念认定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并追究其责任是妥当的。[4]在这一意义上,常识化解释是从法律适用的立场强调刑法解释要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因为刑法所维持和发展的现实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所谓社会伦理规范,按照大谷实教授的理解,是以人们的智慧为基础作为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形成的。行为只要不与社会伦理规范相抵触,就不会侵害社会秩序,也不会唤起社会公众惩治处罚的情感需求。[5]因此,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的刑法解释也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上述两种表述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常识化解释:所谓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实际上是指运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识经验、伦理观念和通俗的生活语言,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应用范围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观说明;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在专业性知识之外理解、接受、遵守和应用刑罚法规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作为关于刑罚法规知识介绍和说明的方法,常识化解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符合生活常识,没有概念的抽象性,不存在专业术语的障碍,对法律条文的分析、论证、推断和结论,都是在常识观念的语境中进行的。在笔者看来,常识化解释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1)解释者以生活常识为基础,从经验的层面勾画、描述和构建刑法规范的可感性模型。例如,刑法第三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大多数教科书都解释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聆听者不必经过专门的法科学习,也无需了解法学原理中的专门知识,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就可以通过这种解释在头脑中形成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象。
(2)运用通俗的语言,将条文中僵硬的文字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多彩的社会现象,将单调或者陌生的法律概念演绎成具体、生动的画面。日常生活语言的普及性,使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进行交流、讨论,不必担心专业术语的障碍、法学基础理论的晦涩,以及法律思维的严谨会对他们理解法律规范带来影响。例如,将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解释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阐述,所以通常是抽象的、晦涩难懂的,以通俗的语言化解概念的抽象性是常识化解释的重要特征。
我们知道,一般公民与司法机关对刑法规范理解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日常用语基础之上的,而汉语的特点和表意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又是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在常识化解释的范围内,律师、法官、学者与社会公众在条文词句的理解上应当是无差别的、平等的,在现代汉语语言表述规则的范围内,很难形成有“高人一等”或“胜人一筹”的“学术权威”。[6]作为刑罚法规的刑法,既约束一般公民的社会行为,也规范司法机关的刑事裁量活动,限制学者们对规范内容以及适用条件的认识。“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验,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协调”。[7]正是在常识观念的范围内,刑法解释的权威性才不被少数的法学家、法官所垄断,人们对法律认识的统一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当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产生争论时,即使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国家审判机关或者法官,也必须对自己的决定作出符合常识观念的解释。
(3)感性直观构成要件与行为事实的符合性。常识化解释可以将案件个别事实与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加以对照、比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理解或认同该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以及依法应当承担多重的刑事责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刑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阐述法律条文基本含义的基础上,说明案件事实是否属于某一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刑罚法规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客观标准,那么生活经验和常识知识就是衡量行为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尺度。脱离感性经验或者不符合常识的刑法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法律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取决于它所作出的规定能否在经验常识的层面上得到普遍的认同、信服,而不仅在于它的强制性。因此,有助于法律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是常识性解释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4)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解释,通常不涉及刑罚法规的本质、规律和价值等方面内容。犯罪构成是违法性和责任的表象,符合构成要件的现象是个别的、感性的、易变的和多样化的,对同一刑法规范的感性认识,可能会因角度的不同而得出诸多不同的结论。而违法性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则是一般的、本质的、稳定的。所以,当现象层面的解释发生分歧和争论的场合,如果不通过科学的解释,往往是无法判断其结论的正确性与客观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的权威解释者是审判机关(在更多场合下是法官),它有权对争执不休的各种意见作出最后的选择。这样一来,“解释效力”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只有在被效力解释接受的场合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的常识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其作用是重要的、可替代的。这种方法在刑法适用和普及法律的宣传教育活动中,既方便国民对法律的理解和遵守,也便于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以及其他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和支持,从这一点上,常识化解释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刑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所谓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是“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普遍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发展体系”,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经验性解说应当以刑法科学的普遍性、客观性为前提,这是科学研究及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二、法律科学中常识化解释的悖论
在刑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有人初学法律,甚至连法理学的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就可以高谈阔论“刑法理论”中某一主要观点,指出法律中存在的各种漏洞和不足;而有人从事刑法教学研究多年,对刑法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感性经验和常识知识的水平。人们不禁要问,刑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生活常识与专业知识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呢?什么是理论?概念思维与经验知觉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有所不同呢?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合是否意味着两者可以混淆或者互相代替呢?笔者不想在该文中对诸如科学、理论、概念思维、专业知识、经验感知等概念作详细地分析论证,但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对这些概念含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随心所欲、任意性的,而应当是规范的、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知识应当是统一的。并且这些内容都是作为一门科学知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刑法专业知识与生活常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常识经验与专业知识是有差别的。专业知识通常是指某一领域中所特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相关的操作程序和行业术语等方面的系统性学问,是从事某种“职业”、“业务”所必须运用,的专门化知识。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受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包括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法律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训练,因为只有通过专门学习并考试合格的人员,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和应用这些知识、技能,才能够胜任具有严格职业或职务要求的法律工作。对于一般公民来说,尽管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自身安全密切相连,所以他们应当对法律有所了解、关心,必须知道遵守法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可是他们大都并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局限于常识和经验的范围,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只限于能够对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作出一般性的判断。当然,随着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但要求再高,也很难达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水准。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刑法是一种职业上的操作规程和制度,法律的适用有着特殊的专业要求和严格的技术规范,并非只是单纯地应合、随附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心理,对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刑事案件,要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做出分析判断,要遵循司法职业技术的基本要求进行裁量,刑事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群体职务行为的操作规范,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履行职责的操作中违反规程,首先表现为一种渎职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我国在现阶段对职业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恰恰说明了法律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性,而不能始终停留在常识经验的水平。
常识性认识是零散的、模糊的、个别的和自发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则是系统的、确定的、普遍的和自觉的。专业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通常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展开的。例如,造成他人伤害、死亡的行为,无论是从常识的角度还是站在专业的立场上,一般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但是,与一般公民的常识观念不同,专业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明,在哪些情况下行为虽然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但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在哪些情况下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会减免或者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能够判断该行为在何种情况下符合伤害罪或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其他的罪名;根据专业知识区分何种情况下是一罪、何种情况下是数罪等等,这些通常是一般公民所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在犯罪性质认定和刑事责任判断等重要问题上,仅依靠公众的常识性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排除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也能讲出符合“人情事故”的道理来说明该行为事实违法、犯罪的性质,甚至十分的生动感人,而且谁也没有权利禁止他们这样理解和解释法律,但在涉及如何公正、合理地行使国家刑罚权力、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常识化理解必须让位于专业化解释。
常识化与专业性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集中地表现在: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专业化解释的规范性、确定性为指导,避免常识观念的任意性、变化性,还是以常识观念为标准衡量专业化解释的合理性、有效性。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实务部门的一些同志存在模糊的认识,而且在学理研究领域也是“见仁见智”。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国民法律情感和规范性意识,主张“刑法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一般国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根据“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行为人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法律的适用,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容及适用应当以司法机关的专业性认识为标准来确定[8]。刑法不仅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作为制裁法的裁判规范,它的遵守和适用直接涉及对法益保护的有效性、及时性,也关系到规范司法、保障人权的公正性、正义性。由于专业与常识之间的差别使得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的适用在某些场合下不相一致,这种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刑法功能的发挥。因此,刑法解释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专业性的知识转化为一般公众的常识观念。
常识化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刑法学的理论问题。理论是任何一门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论,或者相关的知识体系不能被称之为理论,我们就不能将其视为科学。人们通常将书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或者学者们的某些学术观点称之为“刑法理论”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书本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观点通常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特殊问题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说明这类问题所对应的基本原则和普遍原理,因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事例都是偶然的、特殊的”,而理论只关心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刑法学书籍基本上都是从经验或者技术性的层面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围绕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讨论行为所构成的个罪罪名。例如,关于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否要求有暴力行为的实施、是否要求当场劫取财物的争论;企业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性质认定中的“委派”应当如何理解;预谋绑架,采取先杀人后勒索财物的行为究竟是认定绑架罪还是认定故意杀人罪、是一罪还是数罪等等。还有一些书籍采取的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例如,对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解释:在认识方面,必须是明知,所谓“明知”是对自己行为和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有认识;在意志方面,必须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希望”就是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放任”就是对结果的发生听之任之。又如,对“共犯”的解释:共同犯罪也称“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重罪”的解释:是指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自由刑、死刑的犯罪;对法条竞合的解释: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法律条文等等。从这些书籍中我们不但找不到理论性的表述,甚至找不到专业化的痕迹。坦诚地说,笔者并不认为立足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对刑法条文作出通俗的解释有什么不当之处,然而,单就这种解释来看的确毫无理论性可言。
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经验”或者“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那就是理论不是实践。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不是感性认识,不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术、技能,更不是生活经验,如果不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者将他们混同起来,至少是一种误解。应当看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论的严谨性,尽管那些国家的刑法学者们也是以自己国家的刑法典为特殊研究对象,但他们是站在刑法的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立场上阐述法律规范的社会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我们经常以法律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借口拒斥外国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科学成果,甚至以极为轻蔑的态度歪曲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可是这些我们始终在不断批判的基本原理,却时时刻刻地涉及我国犯罪构成学说和刑罚论的知识领域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我国刑法学肯定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却不赞同结果无价值学说的有效性;承认主观故意或过失与客观危害行为的统一是成立犯罪的基本条件,却否认心理责任的合理性;拥护在无责任能力、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能成立犯罪,却拒绝接受期待可能性学说和规范责任的客观性;坚持刑事责任是法律对犯罪人的谴责和否定,却无视有责性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等等。在与外国刑法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中会发现,我国刑法学领域缺乏的是在概念思维指导下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是刑法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导致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刑法作为行为规范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所以,对刑法条文的注释和对法律规范内容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贴近日常生活,以方便人们的普遍遵守;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科学的刑法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作为裁判规范的刑法是针对法律职业群体而言的。对刑法条文的“熟知”与对法律规范的“真知”之间是有区别的,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们对刑法作出的解释并不局限于法条文字的常识性注释,还要对刑法适用的目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等专业性问题有较为清楚和准确的认识;以刑法规范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还要对刑法的“概念框架”、“体系结构”、“价值评判的标准”、“罪刑关系的理论根据”和“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分析、评价和诠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理论的魅力不在于它对刑罚法规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作出如何生动的经验性表述,也不在于从现象层面对个案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演绎多么合情合理,而是集中地表现在它对刑法概念框架的逻辑建构、对罪刑基本关系的思辨和对刑罚价值判断标准的反省。质言之,在刑法的遵守和适用等实践的层面,刑法学中的法条解释只能是常识化、经验性的,而在刑法科学的层面,理论作为条文注释的科学根据、解释规则和客观标准,则应当是抽象、思辨和超验的。
三、常识化的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
刑法教科书根据解释主体的不同,将刑法解释的种类划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这种划分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解释效力的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当人们对刑罚法规的理解和应用发生争论和分歧时,尤其是分歧发生在刑法专业知识的范围时,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为标准理解和适用刑法的规定,将效力解释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正确答案似乎是一条普遍的真理。同时,检验各种意见或观点是否正确,不仅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为尺度,而且必须与效力性解释相一致、相符合。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肯定和支持刑法规范解释的效力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以理论的科学性为根据对效力解释的合理性、客观性做出分析、评价和判断。因为在科研领域中,只有客观、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刑法规范,才能真正地实现刑罚的目的,才具有权威性。由于刑罚法规的客观性、真理性并不自发地包含在效力性解释之中,所以解释的效力性绝不能代替或者等同于“刑罚法规”自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当然,效力解释与科学解释并不是对立的,笔者也无意否认效力解释中的科学性成分,但是科学性与效力性毕竟是有差别的,刑法解释的效力性与科学性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统一和谐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对立冲突的一面。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实现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的统一。无需讳言,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未必合理,而科学的解释因不具有效力而被否定”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刑法解释中,“效力优先”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常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得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和理解统一起来,而效力解释的重要作用恰恰业也在于此。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直接关系到法律社会功能的实现,然而,刑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在于人们对法律认识的一致性、无差别性,更在于社会公众能否准确、客观地认识和遵守刑法规范提出的各项要求。对法律的任何理解都是基于认知主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都会融入认知主体的目的和愿望。刑法解释的科学性并不在于排斥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而是要认真探索和努力实现对刑法理解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效力性解释首先解决了法律认识的统一性问题,而科学解释则更加关注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在正确、客观的基础上统一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刑法的效力解释只有建立在法律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科学领域具有真正的权威性。质言之,引导人们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地理解、遵守和应用刑法规范,是效力解释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刑法的效力解释通常是建立在常识或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经验和常识中的法律是一种表象,现象是不断变化的,除非能够把握它的本质。在经验范围内解决对刑法认识的分歧是难以得出确定答案的,唯一的方法是依赖解释的效力性。而在科学范围内衡量法律解释合理性的方法却有所不同,既可以通过程序的合法性来保障实体的合理,也可以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检验解释的客观性。科学解释与效力解释之间的矛盾是常识化解释必须回答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笔者看来,刑法解释有广狭二义之分,狭义的刑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注释和说明,主要是解决具体事实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问题;广义的刑法解释除了对刑法条文的注解之外,还应当包括对刑法的逻辑结构、概念框架、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客观规律、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建构、辨析、整合、诠释和探索。任何科学都是关于其研究对象的分析和解释,离开了对研究对象的科学分析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领域。换言之,所谓刑法科学,实际上就是对刑法规范整体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学实际上就是“刑法解释学”。刑法科学不但要对具体应用法律条文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更要对刑法规范在适用中的规律性问题与目的性问题作出确定的说明。针对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而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又统一于刑法科学的客观性和目的性之中。
在法律遵守和法律适用中,对法条文字的原本含义作出(典型性)的说明,按照法条文字、词语的一般意义对刑法规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行经验的、通俗的解释,无疑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一旦进入更为广阔的领域,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
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时候曾经指出的那样:常识在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是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9]由于立法技术、社会发展以及立法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疏漏、空缺和滞后性等问题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出现,给刑法的适用和遵守带来一定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结合特定的背景环境和具体的行为事实,对法律规定作出相关的解释和说明时,如果完全从文字的一般含义、条文词语的日常理解来解释法律规范的要求和应用,就会陷入各种疑惑和困扰。也就是说,由于法律规定无法避免的缺陷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规范在其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法律解释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超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的范围,更不能改变刑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质言之,解释的变化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具有确定性、客观性。倘若从常识知识或者感性经验的角度出发,解释的变化性就可能导致对法律条文理解的任意性和解释的随意性,因为脱离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无法检验我们认识的合理性、正确性。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者的主张就是最正确、最合理、最具有权威性的,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的终极目标、客观规律和价值观念决定着裁判者应当如何作出选择。
刑法,是对司法机关和法官追究、裁判犯罪人责任等司法活动的规制和限定,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司法机关和裁判者,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必须根据基本的刑事政策和专业性技术要求解释法律、适用刑法。无论从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司法、审判经验的积累,或者是对刑法的整体性了解以及对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领会,以法官为代表的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与社会一般公民的法律意识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但要反映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与技术规范的确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认知与反省。引导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是法律专业化、规范化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通常取决于他们对法律的需要,希望法律给他们带来安全、保护他们的权益。所以,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从整体上看,对法律的需要大致可以包括三个层次:(1)在行为规范的范围内,一般公民从守法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形成的对法律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保护;(2)在裁判规范的适用中,作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实务工作者,根据各自的诉讼地位从法律应用的角度产生的对法律规范解释和说明的需要,期盼的是解决“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均衡性问题;(3)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内,理论工作者从法学基本原理的视角所萌发的对刑法规范诠释和构筑的需要,探寻的是刑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途径和实质。正是由于对刑法规定理解的各种不同需要,决定了刑法解释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三种需要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在对法律规范理解、遵守和应用上的一致性,应当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和相互融合的条件。片面地强调效力解释的权威性是不妥当的,尽管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笔者看来,真正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基础和条件应当是效力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效力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以客观性与目的性结合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性则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四、常识化解释的合理性认知
刑法的常识化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点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刑法知识的常识化普及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无论在法律实践的范围还是在学理研究的领域,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这种理解上的偏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解释中存在的“专业知识常识化的倾向”,即将常识性认识与刑法专业知识等同起来不加区分,把符合常识观念视为刑法解释的唯一标准和途径,以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社会经验为基准,统一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行为规范的标准指导裁判规范的应用;二是混淆刑法学中职业技术知识和法律科学之间的界限,将感性经验等同于科学理论,坚信“理论”的唯一价值就是直接对应个别现象,解决具体问题。刑法理论应当与生活实践一样,具有直观性、可感性和可操作性。
(一)常识性认识的专业化反省
刑法的专业知识与“人情常理”都具有可感性、直观性的特点,在对具体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时,两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切联系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常识观念中的故意和过失与刑法主观要件的含义十分接近,甚至在典型案例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障碍。然而,当出现复杂情节的时候,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与日常生活用语两者的区别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例如,在防卫过当中,防卫人存在着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要素,同时又存在着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防卫不法侵害的故意,则作为阻却或减免责任的要素,如果不具备后者则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存在与日常生活中故意的不同,还存在着构成要件故意与责任故意的区别。由于我们将常识中的词汇与专业术语相混淆,那么,由于常识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必然会导致法律解释出现分歧和争论。这些问题不但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而且经常成为教学科研领域的主要话题。因此,无论专业知识与常识性认识在某些方面如何接近,两者的界限必须明确。在教科书和司法解释中,或许是为了方便人们对刑法规范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对两者作出严格地区分,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原来所谓的专业人员、学者也是在常识层面上理解法律规范内容的呀!那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社会一般公众是不应当有什么区别的啊!所不同的就是由于职务或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对法律条文更熟悉一些,接触的案件更多一点、相关的司法解释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而已。这样一来,就会经常出现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常识的立场反对和批评熟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和“资深的学者”对法律问题作出的判断和观点(当然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尽管这些批评和反对意见有许多是错误的、可笑的;法律专业人员、学者有时也会脱离专业知识的基本规范,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对法律规范作出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刑法双重规范之间的界限与差别。
刑法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发挥作用的,是对社会公众行为提出的要求和限制。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不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对国民行为的限制和要求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隐含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之中,即只要刑法规定以刑罚方式加以处罚的行为,就是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要求国民以刑罚法规的存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得实施法律以刑罚方式所禁止的行为”。例如,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表面上看,条文只规定了刑罚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得杀人”这一行为规范的前提。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和国民的法律意识,这对于公民接受、遵守法律和预防犯罪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作为行为规范,刑法基本上与社会伦理规范相一致,所以不在刑法规定中明文显示,而只规定有关裁判规范的内容。行为人在意图作出某种行为的选择时,必须能够判断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为刑法所允许,只要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就绝对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刑法保证国民行动自由的重要方面。作为行为规范;从一般人的立场以及根据行为时的事实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刑法更重要的是作为裁判规范约束和规制法官审判行为,从裁判规范的立场出发,刑法具有命令法官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作用。作为规制社会手段的刑法,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约束实际适用刑法的法官的判断和行动,防止根据国家刑罚权任意地适用刑罚,而单纯强调刑法行为规范的特点就会忽视刑法的这种存在的意义,这是值得提防的。[10] 从行为规范的立场,任何背离国民意识、公众观念的法律解释都将被认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或者其他法律职业群体要放弃专业知识和技术规范,无条件地服从公民对法律的常识化认识。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常识化主要是从法律遵守和刑法应用的实践出发的,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性问题转换为公众语言或常识观念,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普遍地接受和认同刑罚法规,引导公民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提出的要求,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实现法律对社会公众行为的规制的有效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常识化解释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将人们对法律的理解限制在常识化的认识水平,或者片面地追求专业知识常识化,将法官的法律素养等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常识观念。
(二)感性经验的理论批判
刑法专业知识在许多方面并不属于理论的范畴,确切的说在这些知识中绝大部分属于未加概括和归纳的感性经验,尽管这些感性认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可能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但我们还是不能够将这些内容称其为理论。
当代法学研究成果认为,法学和法律科学不是同一逻辑层面上的概念,法学既包括法律科学又包括关于法律的学问。而法律科学与关于法律知识的学问,起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11]
其一,从方法上看,法律科学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法律现象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法律知识进行准确(尽量科学化)地表述,而关于法律的学问则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古代社会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我们很难称之为科学,但我们谁也不否认古人关于法律的知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学问。其二,从研究的结果上看,法律科学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规律性的东西,因为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看到的大量关于法律研究的成果,几乎都是仁智之见,究竟哪些成果属于科学的范畴实在难以定论。甚至有学者认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律科学的存在,但谁的研究成果是科学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多数法学著作都可被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学问。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通常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来研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刑法学者,他们对刑法学体系的构造、基本概念的逻辑关系所作出的阐述和理论思维的方法,完全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而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则更多是将法学视为一种职业技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很多人将法学院的法学课程视为一种高级的职业技术训练,也有一部分学者把法学视为关于法律的知识和经验的学问。[12]我国有学者指出,英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验,价值目标是实用;大陆法系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是概念,价值目标是完善。[13]由此可见,刑法学本身存在着专业经验和科学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它们在刑法学中有其各自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从法律遵守和应用的角度,刑法学侧重于实用性、操作性、具体性和经验性,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从法律科学的立场,刑法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刑法的客观性、合理性、目的性和普遍性,是一种建立在基本概念和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由于两者在刑法学研究中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从当代刑法学研究的发展趋向上看,大陆法系国家以较为成熟的刑法理论为基础,更加关注实践操作中具体问题的讨论,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普通法为根基,愈加注重刑法理论层面的研究。[14]刑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既是一门科学理论又是一种职业技能,所以,对刑法的解释既有常识化、经验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科学性、概念性和客观性的一面,两个方面既是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的,又有严格的界限和不同的功能。
刑法学作为职业技术、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在常识观念的领域内是极受欢迎和尊敬的。在这一范围内,刑法条文、司法解释与常识知识是一致的、无差别的,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理解法律或司法提出的要求和限制。“不因不知法而免责”的法谚甚至要求文化水平更低的人也必须知晓法律的内容不得违反规范。在大多数刑法条文中,法律规定是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的,诸如“故意杀人”、“窃取财物”、“放火”、“伪造货币”等等,这些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无需进行解释。有一些规定虽然条文表述使用了行业术语,涉及某些专业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由于是对某一特定领域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尽管一般社会公众可能在理解上会有一些困难,但行为人通常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认识能力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也无需做出特别的解释。例如,经济犯罪中关于违反公司法、金融法规;违反商标法、专利法;违反税法、工商管理法规等规定,对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仍然是现象的、经验性的,并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15]
作为操作规则和专业技能方面知识的刑法学,具有实用性、直观性和可操作性,会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方法和技巧,例如,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上,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个别事实的对照比较,提供曾经被使用过的各种选择方案,推测该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或者可以通过法院以往判决的经验性分析,衡量当前案件事实是否可以适用该法条的规定,甚至将过去的“判决理由”作为该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次,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解释的新动向、新内容,有哪些“司法解释”可以为我们在分析个案与法律条文时提供帮助。经验会告诉我们,司法解释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经验还可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立场上如何变换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有利于自己目的和需要的实现等等。但是,经验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会使概念表象化,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是对刑法规范和刑法思想的诠释与建构,它不但要分析和说明刑法条文中含蕴着的规范内容,还要阐述和论证刑法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可罚性根据。刑法学关于刑法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对刑法的解释展开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学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科学,是一门以刑法规范为解释对象的法律学科。刑法科学的要求是:关于刑法条文的解释应当是实证的、经验性的,作为条文注释根据的刑法理论则应当具有思辨性、先验性的特点。在科学的领域内,常识化解释的客观性、普遍性是受到怀疑的,多变、不真实的经验表象是不能被当成真理而成为科学中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科学解释的权威性高于效力解释,对概念普遍性的理解精确于对经验特殊性的直观,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的客观性优先于“专家学者”们经验认识的主观性。混淆经验性认识和刑法理论的界限,并将此误认为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十分有害的。
【注释】
[1]陈兴良主编:《法治的界面——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论坛》,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页以下。
[2]前引[1],第426.428、434、435页。
[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页。
[4]前引[3],第162页。
[5]前引[3],第69—70页。
[6]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确信自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是正确的,对法官、学者所作出的解释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这种现象说明,常识观念是人们认识统一性的基础,在经验范围内,法官、学者的解释如果不能被常识观念所接受,其正确性就会被否认。
[7]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以下。
[8]关于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究竟以谁的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对法律认识的正确与否呢?教科书认为“行为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通常不影响法律适用”的主张,而行为人作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大多表现为常识化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错误并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法律的认识错误呢?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10](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
[11]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前引[11]。
[13]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页(作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