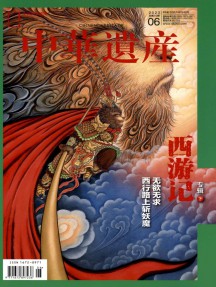汉字与古代文化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10-12 15:35:4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汉字与古代文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其实,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 ”。《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囟声。”其中的“ ”是两只手的变形,农耕需要用手,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囟”又是什么,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 ”中的“囟”并不是声符,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合起来就是“”,也就是草莽的莽,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要想种庄稼,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字形的下面,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正是其中的“辰”。那么,“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古时候没有铁器,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诱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就可以进行耕作,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森林遍布,在耕种播种之前,必定先要砍伐树木,清除野草,没有金属工具,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翻松土壤,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爽也。从从辰。辰,时也。辰亦。”许慎把“ ”当形声字来解释,是他没有真正理解“䢅”的构意。“晨”甲文作、,从辰从二屮,或从二木,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古人农耕非常辛苦,往往是“夙兴夜寐”,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所以,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先写作“ ”,从从辰,表示双手持蜃,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和“ ”中“ ”的作用相同。因此,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也可指除草的工具,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蓐”便又分化出“”;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便又可写作“”。《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
“”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刃广六寸”可知,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之所以可以写作“耨”,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用它作为踏脚,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手耕曲木也,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从形体上可以看出,“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下部是分叉的耒尖,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 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是独体象形字,从形体上看,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也从耒。如“男”字,《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确实是从田从力,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作,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二者形体比较接近,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就不能不说一下“耜”,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木为耜”较耒复杂,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如“耙”、“”、“”等。
篇2
“火”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如、、等,都是像火焰之形的象形字,其上的点画像火星飞溅的样子。火的颜色为“赤”,“赤”字甲骨文作、、等形,小篆作,从大、火会意,大火之色即为赤色。《尚书•洪范》:“火者,赤色也。”在商代卜辞中,“赤”字也多表示火的颜色。也有学者认为,赤字从大从火,其中的“大”并不是大小的“大”的意思,而是像大人之形,从大从火是表示用火来烧人,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刑罚,或者是当时的一种祭祀仪式。《摭续•二九一》中说“贞,勿赤”,赤用为动词,很可能是焚人以祭祀的意思。《铁•一•二》:“癸卯卜,贞,又赤马……”所谓赤马,则可能是焚马以祭祀之义。
与大火相对的是微火,微火最初用“幽”字表示。“幽”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会意,其中即丝字,丝线的特点是比较细微,故从火从正可以表示微火之义。引申为凡微小之称。《尔雅•释诂》:“幽,微也。”如今杭州等地仍将微火叫作幽,这是古代汉语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由于甲骨文中“山”和“火”形体相近,经常发生混同,所以后来“幽”字就变成从山了。《说文解字》中小篆的“幽”字作,从山从,这其实是从火从的讹误。
《管子•轻重》记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学会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如“炙”字,小篆作,《说文解字》云:“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所谓“炮肉”,就是以火烤肉。籀文作,添加了一个表示肉串的偏旁,进一步说明了“炙”的具体方法,是将切割好的肉块用东西串起来进行烧烤。《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毛传曰:“炕火曰炙。”孔疏:“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这些释义正可与《说文解字》籀文相印证。火烤是人们最早掌握的加工食物的方法,后来随着陶器的发明,人们才知道燃火于器皿之下,用沸水来煮熟食物。例如“爨”字的构形,正反映了烧火煮食的形象。“爨”字小篆作,上像两手持釜甑等灶具之形,中间“冂”像灶门,下像两手持木柴添入火中,几个部件组合在一起,正是一幅烧火做饭的画面。
除了用来熟食,火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照明。如“叟”,现在作老叟讲,但其最初的意思是搜寻。“叟”字小篆写作,甲骨文作,上像屋舍,下像一只手高举火把,组合起来正是手持火把在屋中搜寻的形象。隶楷之后,“叟”的形体发生讹变,全然看不出本来的意思了。据《方言》记载,战国时代齐、鲁、卫等国将老人称作叟,《说文解字》也说“叟,老也”,可见“叟”作老叟讲也是很早就出现了。为了区分搜寻和老叟这两个意义,人们便在表示搜寻义时增添了提手旁,写作“搜”。
火在古代田猎活动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原始围猎的主要方法就是焚田。所谓“焚田”,就是以火烧毁丛林草木,使百兽无处隐匿,最终被火围困在中央,便于集中捕杀。《尔雅•释天》:“火田为狩。”郭注:“放火烧草猎亦为狩。”“焚”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林,或从火从,或从火从木,像以火烧草木之形。古文字中从与从林、从木意义往往无别。甲骨文“焚”字还可以写作,这是较为复杂的写法,下面增添了秉持火炬的一双手,但整个字的构意并没有发生变化。商代卜辞中,提到“焚”的时候都是指的田猎之事,这可能是由于上古时代草莽丛生,禽兽繁衍,所以卜辞屡见焚田的记述。如《甲骨文合集》10198片:“翌戊午焚,禽(擒)?”意思是说,第二天以烧山林的方式打猎,能够擒获野兽吗?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不少焚田围猎活动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孟子•滕文公》:“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可见,这种围猎方式在古代十分常见。但是,焚田而猎的方式有似于竭泽而渔,不利于动物的繁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危害,如《韩非子•难一》:“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但在远古那种生存环境中,人们的这种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火在这两件大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字,小篆作。《说文》:“,柴祭天也。从火从。,古文字。祭天所以也。”“”字甲骨文作、、、等形,像木柴架在火上燃烧的样子,周围的点画象征四溅的火星;下面有的加“火”,有的不加“火”,这只是形体繁简的不同,构意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积薪烧之。”邢疏:“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就是烧柴以祭天的仪式。《吕氏春秋•季冬纪》:“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高诱注:“燎者,积聚柴薪,置璧与牲于上而燎之,升其烟气。”燎祭就是将玉帛、牲畜置于燃烧的薪柴之上,用产生的烟气上达于天来祭天的仪式。这里的“燎”就是“”字。“”字形里本来是有“火”的,但由于字形的讹变,其中的“火”看不出来了,为了强调“”与火有关,人们就在“”的形体上又添加了一个“火”,这是汉字顽强地坚持表意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实,在小篆形体中,“”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看不出木柴燃烧的形象了,许慎根据小篆字形所做的解释并不符合“”字的最初构造意图。
火在战事之中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例如《说文》火部:“烽,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意思是说,烽火和燧一样,都是古代望敌情用以报警的信号。在交通极不发达、通讯手段极其有限的古代,一旦边关告急,人们靠什么来快速传递信息呢?火便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无论是白天或夜晚,火都可以靠其光亮和浓烟,将信号迅速传至远处。《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燧火,诸侯悉至。”说的正是以烽火来调遣军队的事。用烽火调动军队,是关系国家安稳的很严肃的大事,但是周幽王却为了博得妃子一笑,竟然用烽火戏弄诸侯,最终招致国灭身亡,为天下人耻笑。周幽王是西周时期最后一个君主,是个荒无道的昏君。周幽王贪爱美色,邻国投其所好,为他选送一个名叫褒姒的绝色美女。幽王虽然对褒姒百般宠幸,但褒姒却面若冰霜,始终不肯启齿一笑。幽王为此十分烦恼。有个叫虢石父的佞臣,替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幽王不顾国家安危,竟然答应了。他带着褒姒登上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警报,以为京城告急,急忙带领本部兵马急速赶来救驾。到了骊山脚下,却见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诸侯们才知道是被戏弄了,纷纷怀怨而回。褒姒见千军万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儿戏一般,觉得十分好玩,禁不住嫣然一笑。幽王见状大喜,立刻重赏虢石父。结果,等到后来犬戎真的打过来时,幽王再命令点燃烽火,诸侯们因上次受了愚弄,这次害怕再被愚弄,就都不理会了。幽王最终被敌兵乱刀砍死,西周也因此而亡。
篇3
不同地区的文明在起源于水边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而不同民族对“水”的认识却可能存在差异。水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像水从高处顺流而下之形。而古埃及文字中的“水”则写作,像水面波纹之形。这两种古老的文字在造“水”字时,同样地直接取象于水的形态,然而却一为竖,一为横。甲骨文之“水”是顺势而流,描绘的是水的流动之貌;古埃及之“水”是平面的水纹,描绘的是静止的水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地貌来寻求原因。我们知道,中国与埃及的地势是不同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发源于西部的高原和山区,顺着地势向东而流,先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于是取水的流动之态而造“水”字。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部,流入埃及后已经是下游,所以埃及地势开阔平坦,支流呈发射状,而非朝一个方向流淌,水面也相对平静,于是以微波荡漾的水面来造“水”字。由于地貌的差异,形成了同样是象形的“水”字,一为竖的流动状,一为横的静止状。另一方面,汉字字形在某种程度上受汉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古人观念中,水沿着河道流淌才是常态,而水横流则是水灾。
水顺着河道而流,可以灌溉天地,为民谋利,故为“水利”。《说文》中有(即“畎”字)、(即“浍”字)、川三字,小篆分别作,,,皆像水顺流之貌,是上古时期的农田水利设施。从形体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是水流大小不同。《说文・部》:“,水小流也。”小篆像一弯小小的水流的样子,表示田间小的排水沟或引水渠。《说文・部》:“,水流浍浍也。”“浍”从水会声,“会”同时也表义,表示会合水流之义,所以“”就是由小水流汇合而成的较大的排灌渠。“川”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形,其构意均像两岸间有流水,故指流通的水。农业文明兴起后,引河水灌溉农田,“川”便成了农田水利设施。《说文・川部》释“川”曰:“川,贯穿通流水也。《虞书》曰:距川。言深之水会为川也。”大意是说,把和等水流深挖疏通,使它们汇集在一起,就成了“川”。《周礼・考工记・匠人》把田间的灌溉渠, 按其大小和所在位置的不同,分为、遂、沟、洫、,最后由汇集成川。可见,在整个排灌系统中,“”最小,“川”最大,中间依次有遂、沟、洫、,一共六级,水利设施非常完善。这说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很早就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目前已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原始水田遗址及其排溉设施,如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邱城遗址中发现了大小不同的排水沟和引水渠。《诗经》中也有引水灌田的诗句,《小雅・白华》载:“池北流,浸彼稻田”,讲的就是用池的水来灌溉稻田。
水横流则为水害。汉字古文字中也有像古埃及“水”字类似的形体,但却是用来表示大水泛滥成灾。甲骨文中有、等形,皆是大水横流之形,表示水不顺河道流淌,是水灾之“灾”的本字,体现了古人“不顺”即为“逆”,“逆”即成“灾”的观念。“灾”字在甲骨文中还可以写作,在“川”中加一横,意为河流中间被堵塞。大水横流,河道被壅塞,水便不能顺流入海,势必造成大水漫溢,淹没农田,摧毁村庄,影响人类的生存,可见古人对水患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在世界各大洲的古老民族中几乎都有关于史前大洪水的传说。在中国,相传在远古时期,上天发大洪水惩罚人类,地面上一片,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躲在大葫芦里才幸免于难,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在西方,则有诺亚带着家人登上方舟躲避洪水的故事。在苏美尔、印第安等许多古老民族中都有这样的神话传说,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始于大洪水传说。
在洪水侵袭时,古人并不是束手待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洪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流传着很多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最为广泛传颂的治水英雄就是大禹。上古尧帝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尧先派鲧去治水,鲧花了九年时间,采用“堵”的方法,没有把洪水制服,被处死了。尧又派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洪水,禹吸取父亲的教训,采用开通淤积、疏浚河流的方法,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洪水。“疏浚”的“浚”又写作“”,其古文字字形正反映了古人疏导河流的治水方法。“”,甲骨文写作、、,从从或,像剔去筋肉后的残骨,旁边的小点是剔下来的肉屑,或是坎。小篆写作,“”省去了旁边的小点并整齐化,坎变成了“谷”字,《说文》释为:“深通川也。从谷。,残也;谷,坎意也。”其中的 由残骨而表示残穿、凿穿,“深通川”就是要用凿穿山谷、深挖隧道的方式疏通水流。这正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大禹治水的方法:“禹别九州,随山川。”意思是说禹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并顺着山势开凿水道,疏通水流。
虽然古文字的“水”取象于水流动形,但古人对静止的水也有细致的观察。静止的水面可以照出人影,所以在青铜镜产生之前,古人就用一盆水来充当镜子。甲骨文中有几个形体:、、,构意均是一个人俯身对着一盆水照自己的脸。这几个形体就是后来的“监”字,本义为以水照容貌。后来发明了铜镜,便在“监”旁加一义符“金”,写作“”字,现在又简化为“鉴”。《庄子・德充符》所说的“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正是用的“鉴”的本义,意思是说没有人用流动的水来照影,而是用静止的水来照。水能忠实地反映人的美丑,这个特点被应用到政治上,就有了《尚书・酒诰》中的名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是以用水照影打比方,说明一条抽象的政治哲理:黎民百姓就像水一样能照出统治者的形象,统治者应该以黎民百姓为镜子来照出自己的政德。
篇4
“陶”是形声字,义符是阝,阝是“阜”字作偏旁时的省变,从“阜”的字意义都跟高地有关。那么,陶器的“陶”字怎么会与高地有关系呢?《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陶,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声。《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所谓“再成丘”,按照三国时期孙炎的说法,是“形如累两盂”的土丘,也就是像两个摞在一起的用土烧制的陶器盂一样,当地因丘而得名,所以地名叫陶丘。这个地方汉代属于济阴郡,大致在现在山东的定陶附近。据说尧最初曾被封于陶丘,后来又迁到唐地,所以才称为陶唐氏。也正因为如此,尧的子孙后来才有的以陶为姓,有的以唐为姓。姓陶的祖先还有另外一支,那就是舜的后代。舜的后人虞阏在周朝时做了“陶正”的官,也就是专管制作陶器之事的官,后来虞阏的子孙就以官为姓,也姓陶。《姓纂》上解释陶姓的来源时说:“陶唐氏之后因氏焉。虞阏为周陶正,亦为陶。”很简要地概括了两支陶姓的来历。可见,“陶”字之所以可以表示高地、地名以及姓氏,都跟陶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陶器的“陶”是因为用来表示陶丘才加上了“阝”字旁,原来表示陶器的字只写作“”。“”字金文作、,右上方像一个弯腰的人形,中间部分表示工具杵,最下面像一器皿,整个字形像一个人持杵在器皿中捣东西。具体是捣什么呢?《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其之用。”《荀子•性恶篇》也说:“故陶人埏埴而为器。”唐代杨注解说:“埏,击也;埴,粘土也。击粘土而成器。”通过捣击粘土而制作陶器,这正符合“”字的金文构形。原来,“”字中的那个人,是在拿着杵在器皿里捣粘土呢!这是制作陶器必需的程序。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学会将具有黏性的土壤捣碎,用水调和,利用土的可塑性塑成各种器物。所选的粘土也是非常讲究的,《释名•释地》:“土黄而细密曰埴。”只有这种细腻的黄土,才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
《说文》对“”字是这样解释的:“,瓦器也。从缶,包省声。古者昆吾作。案:《史篇》读与缶同。”所谓“瓦器”,是一切用土烧制的器具的总称,这一点我们在以前讲“弄瓦之喜”时已经说过。而说“”的结构是“从缶,包省声”,这是许慎没有见到过“”的金文写法的缘故,他把“”字中人形解释为“包”字的省简,这是一种误解。许慎说“古者昆吾作”,是对古代传说的记述。昆吾是夏商之际的一个部族,据说是颛顼的后裔吴回的后代,吴回在帝喾时期成为了南方的部落首领,曾接替他的哥哥成做了“火官”,即专门掌管火的官员。昆吾掌管火,他的后明烧制陶器的技术,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许慎还引用《史篇》说,“读与缶同”,这正点明了“”字与“缶”字的密切关系。“缶”甲骨文作磐,如果再在右上边加上“人”形,就成了金文的“”字了,可见,“”“缶”二字实同出一源,都是表示捣土制陶之义。所以《说文》对于“缶”的解释也是“瓦器”。
缶作为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很常用,多用来盛酒浆、粮食或其他小件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贵重的宝物。所以宝贝的“宝”字中原来就有个部件“缶”。“宝”繁体字作“”,金文作、等,从宀从贝从玉从缶,表示把贝、玉这些宝物储藏在缶中,放在房子里藏起来,由此会合出“宝”字含义。由于“宝”与“缶”古音相近,所以也有学者把“缶”理解为“”字的声符。
缶除了作日常储物的容器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那就是充当打击乐器。《周易》:“不鼓缶而歌。”《墨子》:“息于瓴缶之乐。”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这些记述说明,瓮、缶、瓴之类的陶器具古代经常被用作乐器。受缶类陶器可以充当打击乐器的启发,先民创造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制乐器,如陶埙、陶鼓、陶铃、陶钟、陶角、陶响球等乐器,演奏方法有吹奏、有击奏、有摇奏。在西周初年,人们依据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作八类,即:金、石、土、草、丝、木、匏、竹。这就是所谓的“八音”。其中的“土”就是指陶制的乐器,可见陶器在先秦时期的音乐生活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用手工捏制的陶坯通常做工粗糙,厚薄不均。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陶均。陶均是一种水平固定在短轴上的木质圆盘,人们将陶坯放在旋转的陶均上,在缓慢转动中逐渐修整陶器使之光滑均匀。“均”字从土匀声,它其实是由“匀”孳乳而来的,与“匀”的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匀”的古文字构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我们认为,甲骨文中被人们释作“旬”字的、、等形,就应该是“匀”字,其构形正像将捶打好的泥片旋转着置于陶均之上,其中的一个短的笔道,像用木铲之类的工具将多余的泥片切掉。这样的工具在制陶过程中是很常用的(如图)。由于陶均的作用就是使陶器更加细腻匀称,所以“匀”就引申出均匀的意义,为了与均匀的意义相区别,表示陶均时便加“土”旁作“均”。又由于陶均是转圈的,这正与古代表示时间以十天为周期循环往复的情形相似,所以古人便借陶均的“匀”表示十天,后来又增加“日”旁作,这样就分化出了“旬”字。因此,“匀”、“均”、“旬”三字属于同一字源。
陶器必须用高温才能烧制成功。在制陶的过程中,先民逐渐认识了各种原料在高温烧制下发生的形态变化,当他们尝试用高温烧制金属矿物时,冶金业也就慢慢出现了。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展为金属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陶和冶都需要高温烧制,所以后来二者组合成一个双音词“陶冶”,比喻在困境中磨练培养人的情操。
陶冶的“冶”字,《说文》解释作“销也,从台声”。,是古“冰”字。许慎认为冶炼金属就像融冰一样,所以用“从”释“冶”。但是,考察“冶”的早期字形,并不从“”。战国文字中“冶”的较典型的写法作,从刀从火从口从二。从火很好理解,从刀(或从刃、从斤)表示冶炼而成的器具,而从口从二则众说不一。不少人认为,“口”“二”是羡符,也就是多余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笔画。不过,联系“金”字的构形,将“二”理解为羡符的说法似乎并不能成立。
“金”在古代是金属的总名,并不专指黄金,常见的有所谓的“五色金”,即黄金(金)、白金(银)、青金(铅)、赤金(铜)、黑金(铁)。“金”字金文写作等形,人们对其构形的认识并不一致。但多数人认为字中的两点或三点像金属饼块或矿石之形,右侧下面是“土”字,表示金生自土中,上面的即是“今”字,充当声符。在西周铭文中,“金”有时就写作,足以证明这些点并非羡符。同时也说明,冶炼的“冶”字中的“二”,既不是冰,也不是羡符,而是用来冶炼金属器具的金属饼块或矿石。
“矿”字的古文作。段玉裁解释为“在石与铜铁之间,可为铜铁而未为成者也”,也就是矿石。字的构形应该是模仿矿井的形象。据《周礼》记载,当时就已经有“人”这样的官职,专门掌管金玉锡石之地,甚至在殷商卜辞中就已经出现视凿金于山为国之大政的描述。这说明,矿石的开采和管理很早就受到官方的重视。
冶炼金属的目的就是要铸造各种各样的金属器械。“铸”字《说文》解释为“销金也”。甲骨文和金文作、等形,上面像两手掬着铸器,下面为器皿,器皿内有火。也有人认为前一形体像手持器具将金属液倾倒入器皿之中,这个器皿就是铸造器具的模型,也就是所说的“范”,“模范”二字连起来可以指典型和榜样,就是从铸造器具引申而来的。“铸”字后来到睡虎地秦简时变成了,由金、火、寿三个部件组成,前两个部件表意,后一个部件表音,整个字变成了形声字。再后来,部件“火”省去,就成了现在的左金右寿的“铸”字了。
篇5
饮食进入文化的范畴,要从熟食开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已经在考古资料中得到了印证。自从学会用火之后,人类才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期,从而真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火促进了人类饮食习惯的重大变革,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礼记》在追溯人类与火的历史时说:“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郑玄注:“炮,裹烧之也;燔,加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这里所说的炮、燔、烹、炙,是当时用火加工食物的四种方式,它们的不同特点大致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中得到反映。
“炮”字从火包声,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声音之外,还表示包裹的意义。郑玄注所说的“裹烧之”,也就是用泥巴包裹着食物放进火里去烧,这种加工食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叫花鸡”。关于叫花鸡,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江苏常熟有个叫花子,有一天很幸运讨了一只鸡,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来分享,便将整只鸡连毛用荷叶包裹好,再涂上泥巴伪装起来,胡乱塞入火堆里烧烤,等别的叫花子都不在时,他赶忙把鸡从火堆里扒出来,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惊喜地发现,烧鸡不仅通体金黄,而且味道异常香酥可口,还略带泥土的芬芳,堪称是鸡中极品,从此以后叫花鸡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实,从“炮”的字形以及《礼记》的记载来看,类似叫花鸡的做法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从“炙”的字形看,下面是火,上面是“肉”的变形,再结合郑玄所说的“贯之火上”,可以想见“炙”是将肉串起来,架在火上去烤,估计与现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过,当时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块,有时候也会把整只动物串起来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种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来没有下面的部件,只写作“亨”。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作。《说文》所解释的本义是把煮熟的食物献给鬼神。其字形有的说是像宗庙之形,有的说像盛满食物、上面加了盖儿的器具之形,但各种说法都离不开宗庙祭祀,由此可见熟食与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当时烹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单纯,当时除了要供给人们膳食之外,还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礼》有一种官职叫“亨人”,其职责就是在准备祭祀品的时候,专门负责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锅中水量的多少。《周礼》还有两种和做饭有关的职务,叫“内饔”和“外饔”,“饔”的意思就是熟食,内饔是掌管宫廷内王、后和世子们的伙食的,外饔是掌管祭祀时设计祭品的。亨人在内饔、外饔的工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是食物煮得好坏的关键。
其实,不仅“烹”、“亨”二字本来是一个字,还有享受的“享”,也与“烹”字属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为一形,后来才逐渐分化成三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字。煮食物的意义专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供奉给宗庙上的鬼神,诚意通达于鬼神,这样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闻到祭品的馨香,便欣然享用,这样便有了“享”字。直到现在,方言里还有将这几个字混用的情况,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区称用铁锅烧水为“享水”,用瓦罐把茶烧开叫“享茶”。通过“烹”、“享”、“亨”几个字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烹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饮食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烹”字现在与“饪”连用,构成一个双音词,泛指做饭做菜。但在古代汉语中“烹”、“饪”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而饪则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说文》:“饪,大熟也。从食,壬声。”《论语•乡党》:“失饪不食。”何晏注释说:失饪,“失生熟之节也”。也就是说,煮食物必须熟度刚好,既不能半生不熟,也不能过于熟烂,这样才符合礼仪的要求。特别是祭祀的时候,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标准,是绝对不能用作祭品的,否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烹”“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鼎,象也,以木翼火,烹饪也。”这里的“烹饪”虽然连用,但还没有成为一个双音词,其中“烹”表示煮的过程,“饪”表示煮的结果。“烹”、“饪”相连,构成了食物原料由生变熟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发展到烹煮的熟食法,再到讲究食物生熟度的进程。
“烹饪”是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饮食”则是对“烹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意义,既可以指吃的动作,又可以指吃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对象都可以叫食,最初食是专指主食,“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来的事。“食”字甲骨文作“”,一般认为像一个盛食物的器具,上面像器具的盖子,下面是盛食物的圆形器具。这种圆形的盛食器应该就是“簋”,因为其形象与“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粮等主食的器皿,圆形,上面有盖子,以便使食物保温。《说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这里以“方器”释簋是错误的,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凡自铭为“簋”的器物大多为圆形,因此应释为圆器。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说:“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具体来说,簋的形状很像大碗,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或木制,或陶制,或以青铜铸造。商代簋多无盖,无耳或两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较大发展,常带盖,有两耳或四耳,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簋作为食器已经不很流行,只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发现,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簋”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或,字形的左半边像簋中盛满饭食,右半边像手持匕匙、从簋中取食之形。《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可见簋是古人吃饭的主要用具。
对于“食”字的构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而上面的则像倒着的口,表示人张开大嘴趴在盛食器上来进食。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因为“簋”这种盛食器有时候直径可达几尺,需要借助勺、匙之类的器具辅助,直接用嘴趴到簋上进食是不方便的。
“食”古代经常与“饮”连用,表示吃喝的总称。《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郑玄笺:“渴则予之饮,饥则与之食。”可见,“饮”与“食”的分工是很明确的。“饮”甲骨文作,像人俯首吐舌、捧尊饮酒的形象。其中是人的身体,是酒坛子(即“酉”字),是倒过来的“舌”字。从字形来看,“饮”字的造字意图本来是专指饮酒的。到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中,“饮”字形体中的酒坛子没有了,而是变成了从水今声的。由最初从“酉”发展到后来从“水”,说明“饮”已经不仅仅指“饮酒”了。到了周代,“饮”还发展出与酒相对立的意义:酒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烈性酒,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饮料。例如,《周礼》就专门设有酒人和浆人两职,酒人掌管较为浓烈的酒,浆人则掌管所谓的“六饮”,包括水、浆(清酒)、醴(甜酒)等比酒淡薄的饮品。酒与饮的分称,说明当时酿造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已经能够控制酒味的厚薄,并详细区分其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