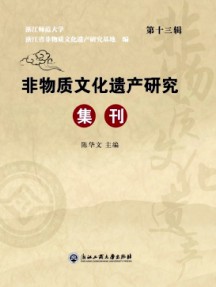非遗文化的标志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10-09 17:41:48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非遗文化的标志,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的表达 文化的文法 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C912.4;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35-07
一、从“有形”到“无形”: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开始致力于世界范围内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78年首批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此期间就有会员国对保护无形的文化遗产表示了关注,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综合概念被引入到UNESCO内部的工作机制中也经历了长期的论证,并于2003年在第32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尘埃落定。可见,从“有形”的物质文化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在世界遗产保护范畴内经历了一次从认识到实践上的文化反思。
以日本为例,早在1950年日本制定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综合考虑了有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文化财产的保护问题,这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较早并在国家法律政策层面的体现和实践。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有着很大的关系。柳田在《民间传承论》(1967[1935])中将民俗分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三大类。在《乡土生活的研究法》中他又把“有形文化”进一步分类为住居、衣服、食物、生活资料的获取方法、交通、劳动、村、组合、家、亲戚和亲属、婚姻、出生、灾厄、丧事、年节活动、祭神、占法、诅咒、舞蹈、竞技、儿童游戏与玩具等共22个子项目。后来他曾延续使用此种分类,但也指出分类具有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应该说,柳田的民俗分类法使得日本民俗学具有了十分宽泛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和层面,并不只局限于民间的文学、语言、艺术和信仰等,也包括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1936年著名民具研究专家谷敬三主编的《民具搜集调查要目》对于生产、生活等物质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柳田和谷的分类对于后来的日本学术界包括文化行政等方面影响很大。1954年文化厅及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在《民俗文化财手册》等文件中也大体是按用途分类的。日本学者一般较多赞同上述分法和文化厅的手册。1954年12月,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告示第58号公布的“重要民俗资料指定基准”如下:A、在以下所列的有形民俗资料中,其式样、制作技术、用法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国民之基础性的生活文化特色且具古典性者:(1)衣、食、住所使用的,如衣服、装饰品、饮食用具、光热用具、家具、民居等。(2)生产、生业所用者,如农具、渔猎用具、工匠用具、纺织用具、作业场(作坊)等。(3)用于交通、运输及通信者,如搬运用具、舟车、“飞脚”(江户时代的信差)用具、“关所”等。(4)用于交易者,如计算用具、计量用具、看板招牌、“鉴札”(由官方颁发许可证的称谓)、店铺等。(5)用于社会生活者,如赠答用具、警防用具、刑罚用具、青年屋等。(6)有关民间信仰者,如祭祀用具、法会用具、奉纳物(供物)、偶像等,还有咒术用具、社祠等。(7)有关民间知识者,如历法用具、卜占用具、医疗用具、教育设施等。(8)与民俗艺能、娱乐、游戏、嗜好有关者,如衣服道具、乐器、似面、“人形”、玩具、舞台等。(9)涉及人一生的,如产育用具、冠婚葬祭用具、产屋等。(10)有关年节行事者,如正月用具、“节句”用具、盂兰盆节用具等。B、在前项所列之有形民俗资料的收集中,其目的和内容等,有如以下各项之一并特别重要者:(1)反映历史变迁者;(2)反映时代特色者;(3)反映地域特色者;(4)反映生活阶层之特色者;(5)反映职业和技能之各种具体情形者。C、与其他民族有关的前述各项所列之有形民俗资料,或在其收集中与我国人民之生活文化在关联方面特别重要者。
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从1962年起进行了民俗资料的全国紧急调查。调查所依据的《民俗资料调查收集手册》(1965年)中的分类项目,包括衣、食、住,生产与生业(农耕、山樵、渔捞、狩猎、养蚕、畜产、染织、手工、诸职),交通、运输与通信,交易,社会生活,信仰,民俗知识,民俗艺能,娱乐,游戏,人的一生,年中行事、口头传承等;并进一步把上述各项内容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从民具的上述分类看,实际涵盖了日本民众生活文化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
在日本现今施行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明确将国家依法保护的文化财对象划分为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和埋藏文化财(地下遗迹和文物)等六大类别。有形文化财包括建筑物、美术工艺品,如绘画雕刻工艺品、书法作品等,无形文化财包括戏剧、音乐、传统工艺技术等。而民俗文化财则包括无形民俗文化财和有形民俗文化财。前者包括衣食住行、传统职业、信仰与传统节庆相关的民俗习惯、民俗民艺等,后者则包括无形文化财活动中使用的衣服、器物、家具等。日本学界的这种分法,显然把民俗文化财作为文化财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单独将民俗文化财再次划分为“有形”和“无形”,旨在说明在民俗文化的保护过程中,如果只侧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不可能将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做到完美,毕竟无形的技艺、岁时节庆等民俗文化往往需要有形的物质民俗作载体,才能将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划分方式所带来的另一个更为客观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语境时民俗文化如何发展?而它的发展实际上应该建立在“无形”民俗文化和“有形”民俗文化遗产共同保护的前提之上。正如在2010年11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上,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在会议发言中所言,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两个重要元素: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理念或信仰,有效表达它们的技艺。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物质或形象及艺术家们诉诸于物质媒介的技艺,所以文化传统的成功传承需要硬币两面的永恒存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相当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附着在物质文化遗产上的理念和文化价 值,如中国的中医、广东的凉茶等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个道理。这就让笔者联想到人类学中对一种文化的定义之观点可以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把文化分为可观察的文化和不可观察的文化。可观察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表达文化或精神文化;不可观察的文化主要指文化的文法。这一分类受语言学的影响,文化和语言很类似,一部分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观察的文化,一部分是不能看得见的文法,是下意识存在的。如我们熟悉中国文化中人的各种行为,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文化的文法。虽然这一分类对于文化遗产而言还是不能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涵盖进来,但它给我们重新分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中,可观察与不可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不过上述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分类在文化遗产的框架下可以重新分类和归纳。如在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中与可观察文化的第一个层面完全吻合,而伦理文化和精神文化应该归入到非物质文化的范畴中。伦理文化是一种道德与制度的规范,而精神文化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些表达的创造又倒过来安慰我们自己,它包括艺术、音乐、文学、戏剧以及等。文化的文法是潜意识的存在,是深化在同一文化个体中内化的逻辑。如昆曲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形式是有空间、具体内容和艺术等文化的表达,但在昆曲分布的地域社会人们对于昆曲本身又是其内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很多的心理文化图式,这就是一种内在化文化,存在于地域群体人们的细胞之中。所以文化的文法应该包含在前文谈到的附着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中文化表达上的理念和价值判断。归纳起来,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文化的表达(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戏剧及像视觉、听觉、味觉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信息等)和文化的文法(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如此定义仅仅是为了操作的方便,其实物质与非物质(原日文称“有形”和“无形”,从日文翻译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就把“有形”翻译成了物质,“无形”翻译成了非物质)不能简单地截然分开,就如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它们还是在一个整体上。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非遗”是一动态的过程。中国的“非遗”理念和政策,也是在考虑两者的有机联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心和边缘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自然和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文化变迁一般是由本文化内部的发展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引发的。其一是文化的涵化,是指不同族群持续地接触一段时间后因互相传播、采接、适应和影响,而使一方或双方原有的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的变异的一种过程及其结果。其二是文化传播,因为在相互、持续的接触中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只有通过大量的相互传播,涵化才能最后实现。涵化强调双方长期的持续互动,双方文化的接触是全面的。另外,涵化过程无法区分涵化的主动方和被动方。最后,涵化的结果是双方在长期互动中通过双向传播或单向传播,使得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变迁。通常变迁先发生在文化边缘地带,然后才向文化中心推进。这种横向的文化变迁过程在文化区的纵深发展即是涵化的过程。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民族文化一直是主导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享有着重要的话语权,有时甚至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话语权。与此相对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层面上,一般就会形成这样的理解,无论从地域分布上还是文化话语权的把持上,都会形成汉文化的“中心”和少数民族的“边缘”。而且在文化发展走向上,通常是“中心”影响“边缘”。多年前笔者曾就“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希望能树立从边缘看中心的意识。其实在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中也应该树立此种意识。特别是在现代语境下,涉及到汉文化的一些非物质文化事项在汉文化的发源地竟然消逝不见;而相反,在所谓边缘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非物质文化事项却得以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如贵州安顺的“地戏”、广州吴川的“飘色”。在这种长期的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的分布和影响力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原来单向度的中心影响边缘的思考,显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2007年笔者到屯堡村寨参观,看到其文化体系非常特别,保留了诸多江南的文化特质。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来源于明朝朱元璋大军的“调北征南”。明朝军队平定南方后,为了统治南方,朱元璋命令大军就地屯田驻扎下来,还从中原、湖广和两江地区把一些工匠、平民和犯官强行迁到贵州安顺一带居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人在亦兵亦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一方面不断吸收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恪守各自世代传承的文化生活习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屯堡文化,既保留了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又在长期的征战耕读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明。而在600多年的屯堡文化环境里,又生存和发展了以傩戏为形态的安顺地戏。安顺地戏的传承虽源自于江南,但经屯堡人移植于黔中以后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成为贵州境内堂戏班子最多、剧目独特、唱腔古老、面具个性鲜明、数量惊人的民间傩戏。它多在广大农村表现,其演出场地皆为村寨内平坝,群众围而观之;演出者均为本地村民自娱自乐,祈福禳灾,并彰显当年屯军之威仪和尚武之精神。同时,地戏这种集体性娱乐活动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居住在少数民族文化优势突出的贵州当地汉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
广东湛江历史上属于多民族或多族群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已经发生了涵化,今天以湛江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早在2000多年以前,汉代徐闻港就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现代湛江因为经济交流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很多学者从整体把握,将以湛江为中心地区的民俗纳入到岭南民俗这一大的范畴中,但如果考量具体的文化事项,我们会发现湛江民俗与广府、潮汕、客家这三大民系的民俗相比,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地方。例如湛江吴川的飘色巡游,飘色是吴川的“元宵三绝”之一。据《吴川县志》记载,清代吴川梅有种色叫“转色”,用一张长方形台,装上一张转动的板凳,中间坐着化妆的少年儿童数人。每年游神时,四人抬着游行,不时停下奏乐唱曲,人们将板凳转一周,谓之“转色”。后来又演变为“板色”,以木板做成色台,用纸扎成花木亭台,所谓色,是一名歌妓坐在台上,手抱琵琶或胡琴,人们抬着游行,经过社庙之处必奏乐唱曲。实际上,从历史源头和飘色活动的全过程看,早期吴川飘色与“迎神赛会”有关,是民众祈求神灵镇邪去病保平安、企盼丰年的原始祭神求福活动。飘色活动在吴川据可考的时间至少也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与之相关的“迎神赛会”显然也与中原地区此类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汉地的迎神赛会常常需要一些童男童女装扮成戏曲中的人物出现在巡游队伍之中,这在江南一带迎神赛会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来看,这种来自 于汉文化主导区域的活动,流传到粤西一带,却和地域文化结合,集中当地工匠的智慧,创造出“飘色”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活动。今天的飘色,既有舞龙、舞狮之类处处可见的传统艺术形式,还有在中国,甚至东南亚地区华人所独有的以傩戏徒刑队伍组成的飘色阵营。
上述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例证有相似之处:从历史溯源上看,都源自汉文化,但是最后得以传承和保留的地域却是在处于西南和岭南的边缘地区,而这些地方却往往被看成是文化的边缘地区。二者在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方面都富有地方色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保留原来的汉文化特征之外,也融入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果按以往的标准考虑,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文化的边缘;如果从周边文化形态的包围和与汉文化区的联系来看,它们也属于边缘。但是,事实上它们目前备受研究非遗方面的学者和当地政府的重视,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护。而反观两种文化事项的发源地的汉文化主导区域,如江南地区,类似于安顺地戏的傩戏以及以童男童女装扮戏曲人物的吴川飘色这种迎神赛会形式显然已不多见。
那么该如何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心和边缘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显然以往以地域和汉文化作为依据划分文化的中心和边缘是有欠考虑的。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近些年来才提出的话题,但是涉及到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等传承和保护却是由来已久。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非遗中的文化事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它是过去发生的。不可否认,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吸取新的内容而形成的,但它是植根于自己民族土壤中比较稳定的东西,有相对不变的一面,能够超越时代而长久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具有新旧交融性。这些非遗文化事项从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是过去与现在交融的结果,渗入了每一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所以如果再用传统的文化中心和边缘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定要超越简单族群或民族的分类体系,要突出地方的概念。又如在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民族走廊的研究,不管是藏彝走廊、河西走廊还是岭南走廊,不同民族或族群创造出各自的文化特性,但同时不同的族群或民族文化又不断地交融共生,形成走廊中不同空间中的共有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很多地方性的文化已超越了固有的族群概念,形成了不同族群或民族共同的地域文化道理所在。所以,我们要看到文化的包容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中体现这种包容性,不能机械地区分文化的中心和边缘。其实,这种中心和边缘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都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文化意义上没有中心和边缘的绝对划分,只有相对的文化中心和边缘。
三、从传统到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的创造、重构
孙家正曾指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目前,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改变了民俗文化产生的原初地理和文化空间,城镇化后的村寨已与原初意义上的农村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现代化过程中,周边城镇和大中城市的辐射力对村寨的发展更具影响力。大中城市的城市文化和中小城镇的城镇文化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村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通过大众媒介、交通运输、商品交易、旅游观光等途径。乡村的文化空间不再封闭,各种文化开始在这里汇聚、碰撞,以前所谓的封闭落后的农村现在基本已经不存在。
而在农村接受的现代文化中,大众文化的影响值得一提。科学技术的发达,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明的引进,都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其在中国这块刚刚开发的土地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加之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经济效益作为其外在的推动力,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完全以大众欣赏取向为主,在内容和价值观上也呈现一种中立化趋势,这都使得大众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形式趋向于某种同质化、普适性、泛众化,更易于被民众接受。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与大众文化的诸上特性存在着很大的不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消逝的速度也在加快。而有的地方由于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竭尽全力挖掘民俗文化的商业价值,又把民俗文化的发展推向了商品化的一端。但过渡强调把文化作为资本的理念,会使某些地区民间文化得以恢复,而有些地方却在式微,出现民间文化创作断代、艺术传人断代的严峻现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民间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实施主体主要是下层民众。行为特点则是高度世俗化;尊奉着在传统中形成的道德秩序;在交往上看重亲缘、地缘等关系;文化传播方式通常是口传心授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俗规约和惯例;其本身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和封闭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已经和即将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大多都是中国各地方、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它们被认为是国家的文化瑰宝,但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却面临着失传和濒于灭绝的危机。如何保护这些民俗文化,关系到民族文脉的传承。尤其是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对于这些无形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最好的方法或长久的发展之道莫过于把它们保护在基层社群之中,亦即创造、解释和不断地再生产出这些民俗文化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土壤之中。
篇2
论文摘要: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工作中,评价标准问题存在着严重偏差,这种偏差在原生态民歌比赛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原生态唱法存在的评价误区,折射出了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音乐评价标准存在着严重问题,这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具有普遍性。只有对评价标准问题及时地予以纠正,打破一元制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的艺术评价机制,才能真正促进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多元的艺术评价机制相伴随的,应是多元的生存方式。只有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非遗”保护才是多元的评价标准、多元的生存方式能够切实实现的基础。
当前国内的“非遗”保护在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其中很多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便是缘于评价标准存在的理论偏差。由于这些理论偏差在原生态理论与原生态民歌保护实践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本文拟以原生态唱法比赛为个案,围绕原生态民歌的理论与保护实践活动,对当前“非遗”保护中的评价标准问题做出一定的反思,以期为进一步的理论建设与保护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原生态理论是一种中国式的“非遗”理论形态,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主要的讨论范围是民族民间音乐领域,与民族音乐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理论对于原生态民歌是这样定位的:原生态民歌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区域内传唱的、较少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的、风格纯正且没有经过加工和提炼的、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并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下来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原生态”一词借用了自然科学上的“生态”概念,原本指的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生存发展状态,把该概念借用到民歌上,应是指附着在各民族、各地区特定的生活环境里的各种民歌形式,与它们的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种交互影响的共生关系。各地相异的习俗、方言、自然地理环境和生存方式等因素,必然导致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具有相异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所以在评价它们时,绝对不能简单化对待,以一种标准统一不同的音乐文化产物,或用一种音乐文化的标准评价另一种……这实际上已成为评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评价原则,也早已是文化研究中的常识之谈。但我们在原生态民歌保护工作中却不断出现违背以上评价原则的情况,尤以原生态民歌的各种赛事表现最为明显,这暴露出了我们在“非遗”评价标准问题上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现在举办的多种所谓的原生态唱法比赛中,在进行评价时,较为突出的现象是用单一标准评价不同的民歌唱法。这种评价误区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以学院派的“科学”唱法的观念来审视、评价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唱法。国内目前被定位为“科学”的唱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西洋歌剧唱法,即美声唱法,另一种是现代民族唱法,这两种唱法的共同之处,都是以西洋美声的发声技法作为衡量尺度,而对原生态唱法的评价,主要以现代民族唱法作为标尺。
首先,撇开对“科学”唱法概念的争议,单就原生态唱法比赛评价过程而言,它完全采用一种刻板、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这与艺术的特征是明显相悖的,因为艺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特殊性,抹杀个性而去追求规范化、标准化,这将无法真实地反映民间艺术的本来面貌。况且学院派的现代民族唱法,从发声技法角度来讲,已不是纯粹的原生态唱法了,它是美声唱法与民歌唱法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民歌唱法,因此以它作为评判原生态唱法的标准,恰与音乐史研究中用古典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品的情况类似,是一种使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完全脱节的、牛头不对马嘴式的批评。而对于原生态民歌而言,其独特的价值与特点,不仅体现在音乐风格、伴奏形式、表演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音乐演唱风格的独特性上,即它是基于不同语言系统、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而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演唱方法。这些在实践中形成的特有演唱方法绝不能简单以“不科学”的评价轻易抹杀,也不能依据“科学”的墨线随意指责。
其次,演唱方法不能以是不是“科学唱法”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论者认为,一种演唱方法的合理与否,其真正的衡量标尺,首要的是看它能否长期健康地生存、广泛地流传,能否经历长期实践的检验,并能世代传承,以及是否能确切地传达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并体现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等。原生态唱法明显合乎这一标准,因为原生态民歌是与各自的文化生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音乐样式,是民族生活的特殊审美观念、审美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它的艺术处理与演唱方法的选择,也完全决定于生活在此文化环境中的审美主体的审美观念,这些艺术处理与演唱方法逐渐固定下来,被世世代代的口头传承。它们对于本民族地区的民众而言,是最美妙的、最合宜的,但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观众可能是无法接受的超乎“常规”的声音。坚持科学唱法的人们也正是这样判断的,这在“青歌赛”中表现得极其明显。一些专家与歌唱家普遍表现出对一些原生态歌手唱法的质疑,较为集中地对歌手声音控制的“度”的问题进行讨论。
而就歌曲演唱“度”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对“度”是否合适的感受,这是音乐审美经验的直接体现,不同民族由于具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对此问题的认识必然会大相径庭。具体而言,每种类型的原生态民歌都是与特定的生活场景、生产样式、生活观念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歌手对歌曲乐句的长短处理、气息强弱等的把握,以及采用的一些独有的音乐表现语汇,完全是由这一文化环境中生成的审美观念来确定的,并无固定的普适性原则。由此,我们说凡是发自歌手心灵的、能传递本民族文化内涵、抒发本民族情感的歌声,对于与之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相同审美趣味的欣赏群体而言,就是最美、最好的歌声,至于一些专家所说的“审美疲劳”的情况对于这一群体是并不存在的。而且部分原生态歌手能在“陌生”的舞台上放声高歌,自由地抒感,进入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基于艺术的表现需要而自然运用的发声技法,无半点斧凿的痕迹,又怎么能认为是非科学的演唱呢?实际上,正是因为相异的文化群体对声音评价标准的不同,原生态歌手那看似“粗糙”、未经打磨的歌声,与学院派的“精致、规范”的声音才相去甚远,也因此在很多专家看来,原生态歌手缺乏对发声技法科学而艺术的把握。但是,我们如对诸如蒙古长调的类似马头琴声音的托腔的发声方法、藏族歌手喉头摆动的发声方法等进行实际的考察,就会发现这类独特的声音竟是由一个没有掌握任何发声技法的人发出的。这只能说明不同的审美观念必然造就不同的发声技法,艺术的表现需要才是发声技法形成的依据。
另一方面,相异的音乐功能,必然对“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原生态民歌在很多民族中是用来满足人们之间交流的需要的,或者是被当做生存活动的工具,是否实用成为它们的首要功能,在演唱实践中,它们往往是“被当做有明确用途的东西”。如有些民族节庆活动中演唱情歌,是为了觅偶;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山民拖着长腔高声喊唱,是为了使对方听见所要传达的信息……凡此种种,音乐的审美、娱乐功能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实用才是首要的目的,因此对于生活在这些原生环境中的人们而言,歌者能发出既实用又“合适”的声音才是最高的表现境界。在此特殊要求下,原生态歌手对声音的审美标准就完全不同于舞台表演的标准了。而我们大众通常所习惯的是舞台、电视媒体上的演出——审美与娱乐功能居于首位的演唱,这类演唱有麦克风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自然要求歌者的音量要适中,气息控制等要适度,由此舞台限定培养的观众同样习惯于舞台式的适度音量与“标准化、规范化”的“科学”唱法,他们对于原生态歌手们发出的超常规的、带有野味的声音,必然会感到嘈杂、刺耳,对于他们运用的特殊演唱技法与表现手法,也必然会感到难以理解与接受,甚至认为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当然在比赛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某些原生态歌手受电视节目、晚会这类演出要求的影响,为片面追求高音而“干吼”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原生态民歌本来就不是舞台的生存物,剥离开它赖以生存的土壤,生命力便不再鲜活了,正如本次大赛的评委李松所言:原生态歌手就像是带泥的萝卜被聚光灯烤煳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看到,我们在试图对原生态唱法做出评价时,要十分谨慎。必须综合考虑它产生的文化生态,包括其产生背景、功能、民族的审美心理、特殊的音乐形态与音乐体系等。用它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它。倘用“科学”一类的词去概括、否定,过于简单,也过于轻率。如果我们仍然局限于单一体系的标准,不但我们不能理解原生态民歌,而且它的真正价值也将被遮蔽,更可怕的是,它们可能将在强势话语的挤压下,改变、塑造自己,去适应强势话语的要求,而自动消亡。[
篇3
关键词: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1 新媒体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体现
近些年,互联网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互联网+”的概念。目前新媒体逐渐被运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在2005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有学者指出,非遗作为一种动态的、活态的文化表现形式,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记录和捕捉的手段要更为复杂多样,新媒体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和文化空间意向,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将非遗展示给大众,这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的系统性、真实性和完整性1。
第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面。陶赋雯指出,目前传播领域正朝着以新媒体为引领以图像消费为主导的方向发展,而非遗本身的一些特点使其在新媒体传播中具备一定的优势,这可以消解非遗传承延续的一些尴尬2。杨青山指出,新媒体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3,并且他指出新媒体与非遗融合的三条路径:一是通过新媒体对非遗进行介绍宣传并及时更新;二是利用新媒体建立非遗数据库便于人们对非遗的了解和查询,并保护非遗的知识产权;三是利用新媒体技术将非遗中的特定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制作4。
第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面。有人认为,媒体文化产品是文化竞争的核心阵地,因此与新媒体结合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文化资源的必然选择5。另外也有人指出,要将可以市场化的非遗通过技术改造推向市场的前台,使之形成文化品牌,走非遗产业化之路6。
在以上论述过程中,新媒体语境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表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通过新媒体,对非遗本身的资料进行多角度的挖掘,从图片影像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非遗进行保存、保护。运用技术保存非遗,这当中体现了非遗的文化价值,此中文化价值并不是狭义文化价值,而是包括艺术、历史和审美等在内的文化价值。因为具有文化价值,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当下运用保存、保护的必要性,才有研究者对其关注。
其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价值。非遗本身是动态的,它通常以人作为承载主体表现出来。而非遗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打破了人与非遗之间的紧密关系,因为非遗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而得到更加全面有效的传播。利用新媒体展示非遗,是对非遗进行建立在现代技术层面上的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展示,可以让那些对非遗感兴趣的人们更系统、全面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近几年来,学术界就非遗产业化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坚持不能产业化,而有人认为产业化是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和传播方面融合之后,加速了其产业化。不管是传统手工技艺中融入机器化生产的元素还是从非遗中汲取某种文化元素进行文化创意生产。在新媒体与非遗融合进行创意生产的过程中,说明非遗具有经济价值,所以才会有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不同群体加入到非遗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直接关系的群体。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笔者比较信服的研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发生关系生成的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价值7。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并不具有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人发生关系之后才具有价值。菅丰指出,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因而与其他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价值。菅丰以日本小千谷市东山地区的斗牛习俗为例进行说明。他指出,斗牛是东山地区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源泉,在斗牛的过程中,斗牛人背负经济压力却依然要购买牛并斗牛,并且在斗牛习俗中,他们并没有获得什么,但他们的行为却为整个东山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除此之外,养牛称为东山人民的生活乐趣之一。在东山地区发生地震之后,斗牛习俗并没有终止,在斗牛习俗复兴的过程中,东山人民积极生活的态度被激发出来8。这简单的斗牛习俗就展示了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多样性。而在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必然也具备这样的价值。
(三)新媒体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表述带来的思考
像部分学者已经指出的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面向所有人,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不同群体。
在新媒体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主要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如果谈及在此情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那么更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更多地存在于广大农村甚至少数民族地区。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就是农民或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往往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主流文化体系的表达没有全面的认知。在经济资本袭卷全球的过程中,这些握有少量经济资本或根本就不具备经济资本的群体就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自己的意愿很少能够得到关注,甚至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恰恰是这些较为边缘的群体承载了对于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前文对于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传播和利用都是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间接关系的群体来完成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却几乎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新媒体中的镜头语言,文字表现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构,重构者却是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他者。尽管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以往而言,能够更加完整系统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但却也将不明就里的人们带入了一个超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状态之中,而失去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常态了解。这种常态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的承载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新媒体似乎切断了这种关系,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展现在人们面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与人发生联系,为人们带来幸福而有价值。而新媒体语境中似乎对人的关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者的关注仍不够。期冀在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的过程中,能将其承载者作为一部分进行关注,并由承载者来推动融合。
参考文献
[1]常凌.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39-42.
[2]陶赋雯.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传播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8):70-76.
[3]杨青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媒体传播价值分析.《传媒》,2014(6)上:78-80.
[4]同上.
[5]刘建华.论数字技术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一体化功能.《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32(6):145-150.
[6]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2015(1):1-10.
[7]菅丰著,陈志勤译.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2009(2):106-110.
[8]同上.
篇4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生产文化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1],因此文化表征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使用记号、符号来传播文化价值和共享意义。传统审美文化中,文化表征也就是“意向”是通过主体的“情”和对象的“景”交融,凝结超越客观物质对象的“气韵”从而体现主体的内在精神追求――即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形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渐步入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即“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2]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进行的不是单纯的功能性和物质性消费,而是一种文化、心理和意义的消费。而随着经济向文化领域的渗透,一方面,世俗的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使得交换逻辑、工具理性成为文化的基本逻辑,低俗的生活趣味入侵了高雅文化的圣地;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消费社会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个人和集体的财富增长与危害同步的恶性循环”,[3]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给生态自然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对文化古迹的过度商业化利用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在消费社会中原本高雅的社会文化被肤浅的现世观念和欲望的快乐原则所取代,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构成也到了急需匡扶的关键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博物馆的价值建构和文化表征才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本文将阐释博物馆在集体怀旧、意向回归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价值,分析博物馆艺术与消费社会中的媒介文化和谐共生,通过仪式传播、意象传播、建筑传播和符号传播方式实现其文化表征的方法与途径,并以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例,试图从生活中找到博物馆艺术彰显其价值和文化表征的现实根基。
一、博物馆艺术的价值体现
依据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分析的趋势,中国的审美文化是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的合力,而博物馆无疑为代表主旋律的主导和精英文化提供了最有力的展示和传播的舞台,为它们在消费社会中与大众文化的博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主体追求感官享受和物质体验,客体则借助文化工业中的机械复制,生产日常和世俗之物满足主体的即时性需求,当主体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客体盲目施压和过度利用时,如对纪念文物、古建筑、古代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开发等,主客体处于一种表象的共鸣而本质的分裂对立的状态中,而博物馆这一珍藏、展示和传播古文化魅力的圣地,可以通过其独特的传播魅力和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重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神性的完美和谐状态,通过唤起消费社会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文化韵味来体现其时代价值。
(一)集体怀旧
怀旧是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怀旧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记忆”[4],“怀旧是某种朦胧暧昧的、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它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好的、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而且也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5]在当今快餐式的生活方式之下劳碌和奔波的人们被世俗的文化裹挟和侵吞,“娱乐至死”和碎片化是现代人们生活的常态,生活情趣和大众文化不断向艺术渗透,未经处理的文字材料、直白的吐槽式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媒介消费而引领流行时尚,长期接受这种流行文化的熏陶会让现代人萌生一种空虚、孤独、不确定和被消解的无助感,而这个时候“怀旧”和传统审美情趣的体验会给予忙碌的人们一种灵魂的归属和心境平和之感。
而博物馆艺术正是人类的怀旧情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一座神圣的“象牙塔”,亲临博物馆与艺术对话的主体会无意识地从现实的集体中独立出来,怀着一颗敬畏和虔诚的心去追寻生命的源头和意识的根基,虽然单个的艺术品很难完成对历史时代的祛魅,但通过与不同时代的多个维度艺术客体对话,也可以避免“管中窥豹”而获得对过去某个时代的整体观感和印象,而指引这一段怀旧审美体验的纯洁的神秘感、理想主义的韵味、诗意化的境界却是最弥足珍贵的是将主体从现实的迷茫、痛苦和喧嚣中解放出来从而感受心灵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灵丹妙药。
(二)意象回归
中国艺术的意象是中国文化独特审美趣味的核心因素,是中国艺术的真精神。清代的学者王夫之认为“意象”是由“情”和“景”的内在统一所构成,是情景交融的产物,而艺术的意象是指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内在的精神活力和外在的外象之气融会贯通、浑然天成而晋升至审美的至高境界。而当今消费社会,这种以意象为核心的古典传统美学被以“仿象”为核心的现代美学文化所取代,传统艺术在消费社会被排挤到“边缘”的境地而面临严峻的挑战。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本文化矛盾》中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6]以“仿象”为核心的视觉影像文化是一种基于技术逻辑和标准化生产的审美艺术,这种可复制性的仿象符号是对物象的极度模拟和仿真,以至于睹象的过程就获得了所指,能指文化的缺席营造了一种虚空和消解的困惑。而现代人长期消费这种艳俗、浮华和浓墨重彩的仿象文化,在满足自身即兴的消费欲望后,难免会产生想象力匮乏、创造力缺失、主体性被侵蚀的心理畏惧,而此时回归到博物馆中静观和凝视其艺术文化--以意象为核心的传统审美艺术的典范――能在沉思和冥想中超越能指和所指的界限,尽情发现意义和感悟当下,从而将自身从视觉文化的技术理性和享受欲望中暂时脱离出来,在独具韵味充满古典历史气息的审美意境中实现心灵的回归和救赎。
(三)文化认同
一个时期的文化代表的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缩影,处在这个时代的民族共同体通过对文化的接触、认知和内化达到对文化的普遍认同,在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的历史规律的砥砺下,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时代更替,民族共同体不断消解或重组从而以新的面貌和形态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这种普遍的认同是国家和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历史博物馆恰好是这种文化自性和民族认同的对象。正如美国学者邓肯所说的那样:“博物馆可以成为强有力的、确定自性的机器,驾驭一个博物馆恰恰就意味着控制某个社会的表征及其某些最高、最有权威性的真理。”[7]
而在消费社会,人们对各种视觉文化提供的刺激和享乐过度消费后处于一种神经麻痹的状态,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分离式发展很容易让人们丧失民族认同、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感,需要思考和觉解某些与现实文化有明显区隔的“陌生”文化来摆脱世俗文化的禁锢。“陌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发现的‘陌生化’原则的体现。即当大众对某种文化已经见惯不惊,甚至产生了‘文化餍足’时,过去曾经流行过但当前已经生疏了的某种文化形态,便有可能重新起到‘陌生化’的作用,从而产生文化上的颠覆和震撼效应。”[8]而此时博物馆呈现艺术品的“陌生化”原则,能使主体参与到与历史的想象共同体的交流和对话中,从当下的社会身份中解放出来并在博物馆的“小世界”中寻找纵向的历史认同和民族自性,继而带着对历史的参悟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重返当下社会群体实现文化共同体的横向认同交流。因此,博物馆的“小世界”不仅可以与历史国家和民族对话来拷问自身的核心文化认同感,还可以在饱受文化震撼之余重返现实“大世界”挖掘博物馆艺术在当下交流与沟通中的价值功能。
二、博物馆艺术的文化表征
博物馆艺术使用各种文化符号彰显和呈现代表“主旋律”的多元文化的表征和意义。而在以消费逻辑为核心的视觉性世俗文化充斥的消费社会,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来的形态,而必须在保持与世俗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中通过不断改变和更新文化的运作方式和媒介表达方式来进行展示和传播,从而适应新的社会传播语境和沟通习惯。
(一)仪式传播
1、仪式传播的含义
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研究的意识模式,他认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一种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额创造、表征与庆典……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9]仪式传播是通过仪式传递信息和表达意义的传播活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一是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其本身的表达内容和传播特性就蕴含着丰富的隐喻、象征意义、群体文化心态、价值规范等信息;二是仪式展示过程中的交流与互动,在此过程中,仪式的参与者与观看者通过仪式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从而获得意义。
2、博物馆中的仪式传播
为了提高博物馆馆藏艺术品的知名度以及博物馆本身的辐射力、影响力和震撼力,通常情况下博物馆会举办开馆仪式或以馆藏文化为主题的庆典等系列活动。这种仪式和庆典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媒介会以凸显馆藏文化为宗旨,借力于世俗文化中的“吸引力”原则和视觉效应,以亦旧亦新的全媒介的传播方式向观众传递亦真亦俗的馆藏特色和文化魅力,很自然的为世俗文化下人们修身养性、返璞归真提供媒介桥梁。除此之外,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的过程中,也会借助新媒体传播的影像互动等仪式完成博物馆学术性、普及性的双重使命。
(二)意象传播
1、意象传播的含义
正如上文中提及的,“意象”是凝结了中国艺术真精神的审美范畴,是相对现世中的“仿象文化”而言的。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传播方式,是古代文论术语,指主观情愿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即是《易传》中的“立象观物、立象以尽言”。意象传播即是能使主体观客体的外在物象就能与之产生内在的精神共鸣和情感交流的一种传通境界。
2、博物馆中的意象传播
博物馆中陈展的艺术品在移位到这个超越时空的“小世界”后,其单个的文化属性就与同一空间中的其他作品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和互补,因此,参观者在观看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时,是在摆脱了现实中的制度和规范的思想束缚后,重新以怀旧、回归或认同的心态与多个艺术品对话和交流而营造主客体相融共生的和谐心象。而单个的艺术品若是脱离了博物馆这个“小世界”语境,这种主客体之间传通交融的境界是很难实现的。
(三)建筑传播
1、当代的建筑传播
建筑传播,顾名思义就是将建筑物作为一种媒介来传播一个城市、地域或某个场所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信息。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建筑文化能代表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风貌和特色,而一些当代建筑往往热衷于追求夸张、刺激的视觉效果而忽略了地域文化底蕴,如因外观酷似一条“秋裤”,苏州的“东方之门”成了饱受争议的“地标”建筑,杭州的奥体博览城的体育馆与游泳馆的建筑因其“创新”的外观酷似比基尼而被网友称为“比基尼大楼”,这两座建筑的外观设计之所以让人大跌眼镜、成为网友吐槽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恶搞低俗的外观设计与苏杭历来的城市地域形象格格不入。
2、博物馆中的建筑传播
博物馆建筑深受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大众审美变异、思维方式局限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其建筑形态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推陈出新。一般情况下,“博物馆形态分为‘意象形态’和‘抽象形态’两种:‘意象形态’是建筑对历史、文化、自然情怀的一种关注和反应。”[10]这种形态的建筑传播与“意象传播”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建筑物这种传播媒介的形态,后者侧重主体参与并与客体情感互动的心象;“抽象形态”是通过对时空和光影等“形而上”的描述突显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色彩,并与博物馆本身的审美情调和艺术气息相得益彰。
(四)符号传播
1、当代的符号传播
结构主义语言学者索绪尔认为符号有能指和所指构成。“所谓能指也叫做意符,通常表现为声音或图像,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对象事物的概念联想;所指也称为意指,即意符所指代或表述的对象事物的概念或意义。”[11]在当今以仿象为核心的视觉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象是对物象的极度模拟和机械复制,得象的过程就是得能指的过程,能指直接取代了指涉物,关于所指的思考空间被急剧的挤压,对符号所指向意义的想象空间也被抽离和省略,因此,当代世俗文化的符号传播是缺乏想象和意念的空间的,是以一种抹杀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张力和差异的一种直接的合一。
2、博物馆的符号传播
博物馆中的符号是以意象为核心的审美文化,意象不是日常生活中直接的对等物,符号是基于文化主题和馆藏底蕴对物象的加工和利用,从而使创造足够的距离和空间使意义的凝聚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观赏者通过发现和感悟符号的意义而与符号创造者达成共鸣,实现创造者分享和传播博物馆文化表征和现实意义的初衷。
三、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文化表征和价值实现
中国文字博物馆以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荟萃中国历代文字样本精华、以揭示古今汉字文化内涵为宗旨,以普及古汉字发生发展与演化的历史规律、引领汉字文化研究的学术规范为使命,是经国务院批准后在2009年11月16日正式开馆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字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以下就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文字之始、文字之旅、文字之家三个部分初略的探究其借助多元媒介展示馆藏艺术品的文化表征并实现其价值的过程。
(一)文字之始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之始,为扩大文字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博物馆在社会各界的震撼力,中国文字博物馆举办开馆庆典暨首届中国文字节。庆典中的各种仪式都通过深情并茂的狂欢活动,活灵活现的将馆藏特色与时代艺术感结合起来,如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幕式焰火晚会、首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暨纪念甲骨文发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字服装艺术展,还有使用贸易杠杆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新豫商、新发展”――百名豫商安阳行经贸活动等。通过仪式活动本身承载和传递的信息象征了河南安阳市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隐喻着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的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所具有的学术地位和价值,而这些紧锣密鼓的活动筹备和热火朝天的集体仪式活动,有利于刺激和激发人们踏入博物馆进一步参观和欣赏博物馆中文字艺术的神秘的好奇心和神往的期待感。
(二)文字之旅
1、字坊
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首先引入眼帘的是字坊这一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高18.8米,宽10米,取材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之形,用殷商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凤鸟纹装饰,因此,字坊集建筑传播中的“意象建筑”和“抽象建筑”于一身:一方面,取材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的形象与消费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各种千奇百怪、让人眼花缭乱的字符有着本质的区隔,后者遵循的是机械复制、刺激眼球的仿象逻辑,而前者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浩渺广博的文化的一种折射和反应,参观者在这气势磅礴、架构巍峨的“字”的洗礼下,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浮想和构思中国文字的浩瀚精深与神秘形象,主体的真实存在与头脑中联想的客体开始对话,博物馆的意象回归的价值在这一睹一思一联想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的光鲜感兼具的饕餮纹、凤鸟纹,以及在字坊前方两侧的同样取材于商周青铜器上的两尊金色铜质凤鸟雕塑,它们都以一种抽象的形态象征着博物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吉祥图腾的社会风貌。
2、甲骨碑林
穿过字坊就是通向主体馆的主干道,两旁是由28块青铜制成的甲骨片组成的甲骨碑林,它包含了殷商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元素――甲骨文和青铜器。从符号传播的视角来研究,28片铜质甲骨片扮演了意符的角色,它代表着二十八星宿,意指就是它所象征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动的指涉着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穿梭在这些碑林中的参观者在陶醉于这些神圣而悠久的古代精神面貌时,博物馆彰显民族自性和文化认同的价值就得以实现了。
3、主体馆建筑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主体馆高32.5米,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饕餮纹、蟠螭纹图案,以殷商时期高级宫殿建筑形象为基本元素。浮雕金顶彰显皇家锐气,红黑图案的雕墙营造一个厚重沉稳、睿智而有涵养、霸气而卓越的展示氛围,是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充分体现。主体馆金碧辉煌的外观与错落有致的外部环境和谐统一,这种以和谐统一为核心的意象传播必然能为参观者营造内心的一片安静与祥和,从而规避消费社会中的各种竞技和冲突带来的内心纠结和矛盾。
(三)文字之家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四个部分布展,分为序厅、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四个部分,共9个展厅。
1、序厅
“序厅主要由四块浮雕组成:北面为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浮雕,东面为中国书法史浮雕,南面为一片甲骨惊天下浮雕,西面为各少数民族文字浮雕。序厅采用天圆地方的理念,穹顶代表天空,周围的灯饰代表星辰。”[12]这种“天圆地方”的理念传播表现和凸显了博物馆意象回归的价值功能。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消费节奏,为了追逐时髦和西欧的后现代潮流,很多标志性建筑都背离了所在城市、所属民族、所归国家的文化底蕴和自性特色,才有了网友集体吐槽的苏州的“秋裤门”和杭州的“比基尼门”,才有了让人们瞠目结舌、大跌眼镜的“武汉汉南区将投资400亿建华中唯一‘欧洲风情小镇’”,不论是与城市的人文底蕴、历史文化积淀大相径庭的现代奢华建筑,还是因过度商业化开发而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根究底,这类让人啼笑皆非的创新之举、经济开发之象接踵而至、屡见不鲜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城市的发展迷失在了消费社会中以“仿象”为核心的视觉影像文化中,逃离了以“意象”为核心的“情”与“景”交融而生的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审美趣味。而代表中国文化深厚积淀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逢时代要求而应运而生,在序厅中,四块浮雕与穹顶、灯饰和谐统一,以其鲜明的层次和结构感展示着“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中国道家的伦理风尚,给身临其境的参观者一次"意象回归"的体验和身心解脱的洗礼。
2、基本展厅
中国文字博物馆内不仅有厚重的青铜石器、浮雕等大型史诗般的力作,还有温文尔雅,娓娓道来的文字与文物的展示。中国文字发展史展厅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展厅。基本展厅分5个展厅,15个单元,从原始的刻画符号到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篆书、隶书、楷书,一直到现代社会的信息时代,全面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刻画符号到文字一统、由隶到楷、说字传义,清晰全面的展示了文字在历朝各代、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演变的全貌,充分体现了博物馆在传承民族自性、提高文化自觉、推动认同与交流上的功能与价值。
3、专题陈列
“一片甲骨惊天下”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专题陈列。“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音、形、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13],甲骨文的造字模式、意向性的造字思维等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观者在逃离城市的喧嚣移步来到博物馆,欣赏这些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字时,一种对古人的智慧的膜拜、对文化的演变与传承的惊叹、对历史的怀旧与思考之情就油然而生了。
4、特别展览
“故宫博物院院藏中国历代书法展”和“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民族文字文物精品展”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特别展览。故宫博物院以灰色顶部、白色背景和亮部的展品,黑色地面三种色调协调配合,一种层次感和节奏感、深邃感和厚重感、光鲜感和时代感便被营造出来,在这样的氛围中品读优雅高贵的书法画作,凝神驻足之刻,通过笔尖和线条中弥漫的文化韵味与历代杰出的书法家进行心灵的交流与沟通,“立象观物、立象尽言”的意象传播之美就酣畅淋漓的浮现出来。民族文化博物馆中展出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物不仅表征了各民族发展壮大、融合演变的历史轨迹,还呈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情,弘扬着学者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民族文化共融的理想主义精神。沉思其中的参观者会对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有一个理性全面的认识,在获得某种感性而真实的文化震撼的基础上,秉承着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参悟和高度的民族自性,再次返回到现世文化中开展横向交流,就会有一种超然世外、怡然自得的情怀了。
5、互动与影像厅
在陈展的过程中,为了借助新媒介的影像视觉传播效果与观众进行更好的互动每个展厅都运用了声、光、电的技术并设置了互动与影像厅,设置了包括猜字谜、数字化汉字等互动游戏。这种互动游戏属于仪式传播的第二个层次上的意义,参观者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与互动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字的魅力和馆藏的特色。
结语
在世俗文化充斥的消费社会,代表“主旋律”的博物馆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话语的存在模式,具有集体怀旧、意向回归、文化认同的价值功能,并以仪式传播、意象传播、建筑传播、符号传播的新旧媒介融合的传播方式展示其文化表征,建立民族自性、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代表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其陈列布展和建筑设计中充分展现了博物馆艺术的价值和文化魅力,其审美功能和文化机制对我们超越消费社会中的欲望喧嚣造就的感官和仿象审美带来的精神空虚,从而获得心灵的归属和惬意是有所裨益的。寄希望于今后博物馆艺术能更加精深而宏远,踏上文化“走出去”的脚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让更多的人学会用意象的视角、诗意的心态来审美。
注释:
[1]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刷馆,2003年,第15页
[2]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4]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5]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
[6]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页
[7]丁宁.艺术博物馆: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浙江社会科学2000(1).
[8]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
[9]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国传媒大学学术研讨会文集,2007年5月
[10]阳洋.意象与抽象――博物馆建筑形态构成初探[J].重庆大学,2004年5月
篇5
〔关键词〕湖南 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文化空间
湖南人民在长久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体现了湖南区域乃至江南一带传统的审美与价值观念,也凝聚了这一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量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性开发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门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多年依靠口头传承、言传身教,大多处于人存即存、人亡艺亡、人去歌息等境况,对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十分不利。而当前的保护与传承措施往往流于形式和眼前,缺乏从理论高度和长远考虑出发的视角。为此,本文拟以文化空间为视角重新探讨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文化空间视角的提出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掀起了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对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政府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如何保护、如何传承,尤其是以什么样的原则、立场、理论进行保护与传承,一直是相关部门、学者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他们吸收了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地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从自身学术关注与追求出发,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给予了丰富且有价值的论述。其中,从国外研究引入的文化空间理论视角颇受学术界重视。[1]
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即是“文化空间”,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概念。其内涵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事物的集中体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的集中场所,也是举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特定时间。有的学者将文化空间提升至人类学的概念范畴,认为它是人类文化有规律性表达的地方。无论对文化空间的定义如何展开――是从地理上亦或是从抽象上,它都离不开四大关键要素,即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
在文化领域,象征是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文化独特性表现的意象载体。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至少有一个核心象征,它是该空间中所有成员认同的意识基础。至于象征到底有什么物化表现,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象征,这种象征是否关系到整个文化空间的演替、兴废或变革。与象征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要素是价值。文化空间中的价值是所有成员的精神创造与积淀,对文化空间内的行为方式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价值的缺失,意味着文化空间将在不协调中陷入混乱。所以,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价值的保护,它与象征一起构成了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说象征和价值是文化空间的抽象表达,那么符号就是文化空间最为形象和直接的表达了。诸如民族歌舞、服饰、饮食、建筑等都是文化空间中反映文化特性的符号。它是象征及价值的外在物化,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文化空间与文化本身一样,是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产物。记忆既是文化空间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由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构成的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对象,因而也是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
二、即有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湖南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底蕴深厚、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独具风味。据不完全统计,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有近三万个,其中,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占据了一半以上,形成了湖南区域独特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2]
(一)音乐文化空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反映民族价值、精神、力量、意志、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从来不乏优秀的音乐文化资源。湖南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新化的山歌、麻山的锣鼓、桑植的民歌、澧水的号子、苗族和土家族的民歌等等。举例而言,在湖南湘西的苗寨,民歌有“五腔十调”之说,每种腔调都有不同的演唱方法和技巧,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符号。“五腔十调”所表达的喜悦、悲伤、平和等情绪既是民族集体或个人情感的象征,也是对音乐的价值赋予。苗寨的山歌和湖南其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实践和艺术沉淀并传承下来的,是集体或个人历史记忆的一项艺术单元。
(二)舞蹈文化空间。湖南境内各个民族都拥有象征各自生活、风俗、劳动习惯的传统舞蹈。在邵阳、怀化、永州等地区,不论婚丧嫁娶,还是赛会迎神,亦或是农闲时节,舞蹈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湖南的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瑶族的长鼓舞、张家界的高花灯、苗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汉族的龙舞和狮舞等等。举例而言,土家族的摆手舞充分展现了这一古老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舞蹈动作象征刀耕火种、民族迁徙、捕鱼狩猎、传说神话、古代战事等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土家族的另一项传统舞蹈――茅古斯舞,更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和“中国民族舞蹈的源头”。这种舞蹈记忆的历史传承在当今诸多研究者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充分证明了这一特定文化空间存在的悠久而深厚的底蕴。
(三)戏剧文化空间。湖南的地方戏剧历来都是中华戏剧艺林中的一朵瑰丽奇葩,花鼓戏、花灯戏、武陵戏、苗剧、湘剧等长期绽放于中国剧坛。举例而言,邵阳的布袋戏,集戏剧、木偶、表演等技艺于一身,具有新奇、精致而不失神秘的艺术魅力。而邵阳一带的苗戏和侗戏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成为我国民族戏剧文化中的独立品种。这两种少数民族戏剧综合了说唱和歌舞艺术,不仅承载了苗族和侗族的传统文化与审美情趣,还象征着两族人民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生意识,成为两族人民绝不会遗忘的历史文化记忆。
(四)曲艺文化空间。湖南的曲艺文化与其他中华传统曲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民间歌唱艺术及口头文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型和成熟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而湖南的曲艺形式可谓种类繁多,已知流传过和现存的湖南曲艺种类就超过三十种。湖南的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长沙的弹词、常德的丝弦、瑶族的谈笑等等。举例而言,湖南四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以长沙方言为语言符号,以塑造人物故事为艺术主题,靠艺人的自弹自唱来反映长沙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具有几乎与长沙城一样悠久、鲜明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挤压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
尽管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魅力无穷,但不可否认,其文化空间正在因多种原因遭受挤压、面临挑战,从而不同程度影响了不同种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3]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措施多,实际履责少。当前,湖南境内各市县区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普查、申报等工作都比较重视,但这些工作往往不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当普查和申报结束,相关工作机构即被撤并,工作人员也大多返回到原来的本职工作中去。根据调查走访的结果,很多相关机构办公室要么没人上班,要么只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室内空空如也,更有甚者连专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如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研究人员、从业人员的研究与职业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只能停留在文件中,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
(二)传承有困难,状态无改善。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在受保护的平台上能获得定期的、有计划的演出是保障生存、实现传承的基本手段。然而,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既缺少平台,又缺少计划,它往往只有在应邀参与红白事演出的过程中才能与人们见面。此外,由于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表现形式都是以古老声腔或简单舞姿为载体,很难吸引年轻人拜师学艺。而年长的艺人们也很少以此为生,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务农或经商上方能保证家庭经济来源。在湖南,除了那些最有代表性或影响力比较大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外,很少有艺人能获得相关生活补贴。缺少基本生活保障,让实际负责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们难以安下心来表演和传承,更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一文化遗产的未来。例如前文提到的邵阳布袋戏,目前获得正式承认的传承人只有一位,这项文化遗产不得不面临断代甚至灭绝的窘境。
(三)矛盾未厘清,原味渐消散。多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一直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后人对此能做的只有保管好它,并把它原封不动交给下一代。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现代科技和现代意识的作用下被创造、包装和发展。例如湖南的花鼓戏,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早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演模式和艺术记忆。而现在当人们一提到要保护和传承花鼓戏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创新发展花鼓戏以适应所谓“时代的要求”。如此一来,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中的“胡大姐”在很多演出场合要么打扮得时尚靓丽,要么穿着艳丽妩媚,原本勤劳智慧、朴素善良的胡大姐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被艺术新潮流包装得五光十色的新人物,“遗产”失去了它原本的底蕴和韵味。
四、拓展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境,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只有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高度,以扩展文化空间为切入点,才能为这一保护与传承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4]
(一)注重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包括湖南在内,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存在一个误区,即将关注点集中在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客观割裂了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从而忽略了它们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同样存在这一误区,既缺乏历史纵向的联系,又缺乏空间横向的串联。例如湘西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文化从来不存在时空上的绝对隔绝和独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们的象征意义、价值观念、艺术符号、集体记忆等多有相似之处。既如此,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就不能各自为阵,而要将它们放在一个大的文化空间背景下加以对待,保护它们共同的象征、价值、符号和记忆。
(二)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关于文化空间的生产观念是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贡献之一。其核心内容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要坚守传统、保护古旧固然值得提倡,但绝不能无所作为,必须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传递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价值,使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物或承载物得以继续存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在文化空间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广泛认可的保护理论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空间的生产并非要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它更多偏向于文化的复制,既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延续性和观念延续性,又扩大新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就是要将诸如苗寨歌舞、侗族戏剧等带出偏远的深山,通过新兴的媒体宣传手段原汁原味复制给更多的人欣赏,让他们在了解中接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韵味的熏陶,在接受与熏陶中自觉保护和传承这一遗产。
(三)扩大文化空间传承需求。正如前文所言,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物质动力,也就缺乏人才资源。有鉴于此,要尽量开拓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要广泛调研和认真研究原有文化空间中的原住民和新开拓文化空间中的现代人,他们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渴求和生活质量要求。单纯注重物质、经济要求和利益是不能为传承提供不竭动力的,只有在加大宣传和复制力度的同时充分获得文化空间内人们的反馈信息,才能及时了解和把握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处的空间环境,进而有的放矢采取补救或助推措施。例如对长沙弹词的传承,绝不缺乏会说长沙方言的年轻艺人,需要思索的是,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他们吸引到合适的艺术学校教育体系中,有规律、有计划、有目标地传承该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面临保护与传承困境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下,认真审视不同文化表演形式的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要素,注重整体保护、融入生产观念、扩大传承需求,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出表率。[5]
参考文献:
[1]顾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2-43.
[2]刘鸣泰.湖湘文化大观[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3:1-3.
[3]孙文辉.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