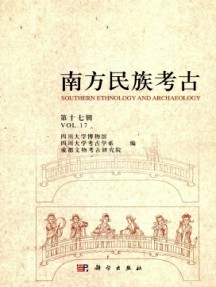地域文化的特征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10-09 15:05:3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地域文化的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据史志记载,遵义地区在历史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属泛称的“西南夷”地域。史学家普遍认为,濮人(仡佬族)是黔北土地上的原生民族,今天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就是仡佬族的大本营。从古至今共有仡佬、苗、土家、布依、彝、侗、回族等38个少数民族在黔北这片地域上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如仡佬族、苗族、彝族等在一定的地域内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语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习俗、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因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在文献记录的内容中都显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如黔北各县市的地方志中都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相关民族的族源、经济发展、语言文字的产生、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是今天我们研究了解该地区民族的借鉴和依据,也引起了研究该地区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视,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闻名遐迩却濒临失传的危机,如桐梓的“蛋画”、遵义的“核雕”、赤水的“竹艺”等。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遵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根据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关于搜集、整理、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指示精神,历经10余年,编纂出版了300万字的《中国歌谣•遵义卷》、《中国故事•遵义卷》、《中国谚语•遵义卷》、《遵义花灯音乐》等书籍,受到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的赞誉。
(2)地方志书代代赓续,成果斐然
聚贤修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地方一大盛事。黔北也不例外,自宋、元以来,地方志书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据文献记载,黔北在以往六七百年间撰就多部志书。现已不存的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到了清代,在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三部优秀府志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该志的体例最为科学完备,誉之为“府志中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也认为该志可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齐名”。黄万机对《遵义府志》作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卓出众家,独具特色。总之,《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中,都堪称上乘,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民国年间,先后由杨兆麟、赵恺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记述了清末若干史实,可供编写新志作为翔实的参考;抗战时期由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开创了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上列的几部珍贵的典籍皆为黔北地方文献中的传世佳作,享誉志林。就现今而言,涉及黔北各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同样俱全,为学者研究黔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3)口头文学丰富,口传文献比重大
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寓言、歌谣、文人文学等文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导致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很少,多为口传文献,是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才得以留存至今。如在道真、务川一代口头流传的苗族喜唱的盘歌,很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苗族的诗歌作品广为流传,民间歌谣有古歌、叙事歌、礼仪歌、劳动歌、情歌、山歌等,谜语在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为口传心记;侗族的文学多是口授言传流行于民间;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改土归流后,随着彝族地区君、臣、师三位一体地方政权的解体,仅一些布摩按世袭家传的禁忌令,将祖传的历史文献袭传,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殆尽。现已搜集和翻译的神话、传说故事有数十个。现搜集的口传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学、宗教、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找到所需的内容。贵州民族学院编印的《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传说集》,载有黔北地区口头流传较广的神话、人物、风俗、地理、物产等传说故事60多个。
(4)浓厚
篇2
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篇3
关键词:湘西苗族;舞蹈;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160-01
湘西苗族舞蹈历史悠久,它来源于苗族人民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苗族人民为了生存,在荒山野岭之中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在精神以及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苗族人民仍然对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在闲暇之余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舞蹈艺术。这种舞蹈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巫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湘西苗族人信巫好巫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他们拥有独特而体系完备的巫教文化。对湘西苗族的民间舞蹈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其与巫在很久以前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苗族舞蹈是原始表情手段的表现形式,从诞生之初就与苗族人的劳动、战争、娱乐密不可分,随着它们的发展而发展。湘西文化之所以守成受动与当地贫困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巫风盛行就是其突出表现。湘西苗族舞蹈的动作、神态甚至装饰都可以看到巫术行为的影子,此可谓“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可以说,湘西舞蹈与巫术的文化根源是一致的。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缺乏准确的认识,认为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而人们又普遍希望遇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于是开始求助于神灵,以歌舞作为娱神的手段,祈求神灵能够赐福人间,对自己加以庇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宗教性的歌舞聚会,这也是歌舞表演最原始的状态,对于促进原始艺术的发展及走向成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苗族舞蹈在苗族社会生活中渐趋物态化,一直到现在都与其社会习俗和糅合在一起。因此,难以从单个层面上来理解其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有学者认为巫术是湘西苗族舞蹈的起源,这种看法虽然比较武断,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巫术与苗族舞蹈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实情况来看,苗族民间舞蹈仍然比较纯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日趋功利化,苗族民间舞蹈会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在湘西苗族巫术包括了一切,这是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
二、耕猎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作为最早的农耕民族之一,苗族早期活动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在这里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繁衍子孙,开创文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苗族舞蹈也就很自然的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崇拜活动中具有浓厚的农耕色彩。湘西苗族舞蹈在表演内容方面就记录了其先祖的生产活动,质朴的再现了他们的社会生活画面。
农耕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繁荣,民间舞蹈也因此应运而生。最为直观的是在湘西苗族民间舞蹈中,民间祭祀活动、原始猎兽场面以及庆祝丰收等情景屡见不鲜,有的舞蹈内容还与兽类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苗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历程来获知苗族农耕文化的原始形态。苗族民间舞蹈无论是类型还是动作都取材于与农业有关的日常活动,在这一时期,舞蹈风格也不再像原始舞蹈那样拙朴粗糙,而是渐趋华美和精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可以这么说,湘西民间舞蹈已经成为反映苗族先民原始生产生活的一面镜子。
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生活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演变,鱼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这种风俗却得以世代相传。探究众多的鱼猎文化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猎神崇拜作为苗族人的原始信仰是在鱼猎生活中形成的。由此可知,鱼猎生产在苗族人早期的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农耕时代开始之后,鱼猎经济成为农耕生产的重要补充,而其相应的猎神崇拜习俗也沿袭下来。传说在围猎之前一般会有祭祀猎神的舞蹈,这种舞蹈就是苗族的木鼓舞。从表演形态上来看,苗族民间舞蹈具有线条粗犷、动作朴素的特点,同时也颇具野性。它来源于苗族先民原始的狩猎生活,反映了他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表演的动作和情节来看,苗族民间舞蹈蕴含着丰富的原始鱼猎文化元素。
三、歌乐文化与湘西苗族舞蹈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苗族民间舞蹈也在不停的发展和进步。苗族舞蹈在应用方面不再局限于宗教祭祀活动,在各种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以及日常交往中也都能看到苗族舞蹈的表演,逐渐成为苗族人民交流情感、表达欢乐的群众性舞蹈。
苗族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就反映和表现了苗族先祖灿烂丰富且充满神秘气息的民歌文化。由此可知,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苗族先民有崇巫信鬼的文化传统,他们好歌好舞,有声有色的表现了巫歌傩舞的艺术形式和特点。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苗族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不仅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上独具特色,而且还成功的将舞蹈和歌乐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歌、舞相得益彰的歌乐文化。它主要分为祭祀仪式和娱乐两方面的内容。
苗族的歌乐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还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苗族人民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将歌乐与舞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湘西苗族地区,尤其是群体场合,常常是歌舞相伴,唱和相继,很容易形成热烈的气氛。
四、战争与湘西苗族舞蹈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战争始终如影随形,战争已经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给苗族人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上古时代开始,苗族舞蹈就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战争场面,以武舞为主,文武糅杂是苗族传统舞蹈的重要特点。苗族部落经历了从远古时期到明清之际的无数次战争,在战争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苗族社会文化,必然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文化也是如此。如“猴儿鼓”活动据说就起源于部落战争时期,苗族先民用鼓声来鼓舞士气,激励苗族勇士们奋勇杀敌。从这方面来看,苗族武舞以一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对古代战争进行了叙述,从其动作姿态上来看具有很明显的操练以及征战性质。
五、生、死与湘西苗族舞蹈
生死观是人类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生死观价值评价也不一样,湘西苗族人的生死观可以从“踩鼓舞”上得到充分体现。苗族人民主要生活在高山地区,平常爬坡上坎上山下山时,从他们的身体姿态、步调可以看出他们有一整套比较协调的习惯动作。谙熟苗族人生活规律和习惯的人不难发现,他们的行走特征隐含着“踩鼓”的韵律。一定的文化特征和习惯都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苗族人的这种行走韵律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是民族特征的自然流露。
不同民族对丧葬有不同的理解,在丧葬方式、丧葬价值观上也存在区别。苗族在近代以来倡导土葬和洞葬,在停棺期间一般都要绕棺而舞,以“踏歌”、“闹尸”的简练方式表达一种长寿、吉祥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这种强有力的生命节奏能够激荡人的心灵,也表达了人类共有的心理倾向。
六、总结
综上所述,湘西苗族舞蹈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性,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湘西苗族舞蹈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舞蹈与音乐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社会历史与人类情感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以及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熊晓辉,郑艳红.湘西苗族民间舞蹈的文化本源[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篇4
武当武术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与武当地域文化相互激荡过程中,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由张三丰为代表的历代武当拳师在探索武当武术技击之道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仅包括与武当武术密切相关的武当武术传承流派、武当武术拳术与器械、武当武术技击功法理论等外在文化产品,以及蕴藏在上述主要内容之中并且主导其创造活动的拳法自然,由拳悟道,由内而外,由术入道,崇祖尊师,循宗问道等内在文化精神,还包括由这些基本内容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武当地域文化内容,以及由这些基本内容所延伸出来而体现在其他地域武术或武术门派中并与它们共享的文化内容” 〔1〕。武当武术文化是以道家哲学思想、道教精神为基础,融入儒家、佛家、中医学、兵学、导引、养生等思想,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荆楚地域文化的孕育下,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而沉淀下来的物质和文化的综合体〔2〕。
所谓地域性就是指与一个地区或区域相联系或有关的本性或特性。对于某个特定的地域,其中一切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就表示为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特征就是当特定地域所具有的共性体现在武术文化上,就成为武术文化的地域性即地域性特征。
2武当武术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
武当武术的产生和发展,与武当山特殊的地理环境、武当山道教神祀、元明时期的政治经济、道教气功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武当山,又名参上山、太和山。其作为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内家拳发祥地,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市南部。它发源于秦岭山脉,属巴山东段支脉,耸峙于鄂、豫、陕、川交界处,诸峰骤起,层峦叠嶂,雄峻峭拔,长江南绕,汉水北回,东瞰江汉平原之西陲,北接秦岭之南麓,绵亘八百里。武当山山势雄丽,风景幽奇,具有“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奇特景观。它以其景色宜人的特殊地理环境条件,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历来祀奉北极玄天上帝。宋真宗因避尊祖赵玄郎讳,改玄武为真武,号称“北极真武帝君”。武当形胜,千百年来引来无数羽客高士。其著名者周有尹轨、汉有阴长生、晋有谢允、唐有吕洞宾、宋有陈抟、明有张三丰等。明初国势强盛,在这个时期武当山宫观建筑和神祀宗教活动也达到了鼎盛,这是与明初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发展分不开的。然而,武当的兴盛,又与明代崇奉道教有关。庞大的道观建筑群的兴起和神祀活动的大规模化、经常化,为道教的昌盛、道藏典籍的辑印、道教气功、武术、医药等发展开辟了天地。武当道教的兴盛,又促进了道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玄机秘法的归宗,珍贵的丹道遗产,为张三丰准备了可参悟、借鉴的大量资料;武当武术的缘起,则是张三丰诸家先哲之睿智而形成的。信奉道教教义的仙道、文人墨客,出于对成仙得道的穷极追求和长生久世的探索需要,将丹道功法融会贯通到了拳艺之中,促进了内丹术功法与古代武术技艺的有机结合;历代高道异士,又以道家之哲理阐释于武当武术之技理,逐渐形成了从功法到理论都蕴涵着独特哲理和精妙拳技的武当武术,张三丰好道善剑、学识渊博、深通技理之奥妙,在当时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基于道教管理和道士自卫防身的需要,以道教内丹术的宗旨为出发点,集内丹术与武术技击为一体,升华和创造了客观需要的新的技术理论体系,为武当武术的形成做出了集大成的贡献〔3〕。据武当拳法研究会提供的资料表明,自元末明初起始,《张三丰太极十三式》等武功典籍业已流传,武当丹派、松溪派及其他庞杂的武术、道门流派如雨后春笋,武当弟子已遍行全国各地。可见,武当武术是从武当山客观的历史、地理条件和道教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诞生的。
3武当武术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3?郾1武当武术文化圈
“文化圈(cultural circle)是一个文化丛存在的地理空间。文化圈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这一整体的文化元素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它包括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等文化的一切主要范畴,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永久性。”〔4〕武当武术文化是地域文化学的重要内容,即“武当武术文化圈”,是一个地域文化,其地域应以武当山为中心,辐射涵盖整个十堰市的行政区划,以及襄阳、神农架等地。武当武术文化圈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板块。武当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生态文化圈建设中处于龙头地位。以其为核心,可以登武当、探神农、品三国;整合道教文化、建筑文化、汽车工业文化、森林探险、汉江风光等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濡化”过程。武当武术文化在其形成的自然地理空间中,不但受到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道教文化、山区文化、移民文化、儒家文化、军事战争等方面,其中道教文化在武当武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道教文化是指凝结了道教精神的一切存在,是一种以性命之学为根本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经过几千年来无数先贤的探索、实践和发展,形成了思想深邃、方法独特、结构完备的道教文化体系,它在探索人体和自然奥秘、生命根本问题方面达到了极为精深的境界〔5〕。而武当武术主要是通过方士体系与道教发生密切联系的。方士体系是春秋战国大变革的产物,其信奉中国古代特有的神仙思想,认为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可达到长生不死,肉体飞升成仙的效果。经过先秦方仙道、秦汉黄老道而为道教所继承。武当武术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中国道教文化土壤,成为道教养生文化中的代表之作、经典之篇,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武术作为武当地域文化系统的分支,是道教思想滋养与孕育的结果,其在拳理技法上不同于其他派系武术,具有独特之处。在漫长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武当武术与武当文化各个方面具有或疏或密的渊源和关系。武当武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隐含有浓厚的武当文化历史印记,武当武术也将成为反映和表达武当文化的符号和语言。
3?郾2武当武术文化丛
“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上相互联结、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集合体”〔4〕。文化丛 通常以某一个文化特质为中心,结合一些功能上有连带关系的特质而组成的,其中每个特质都围绕中心特质而对整体发挥功用。这样的文化丛总是冠以中心特质的名称而称为某文化丛。武当武术文化丛亦是如此。武当武术文化丛是以武当武术为中心,包括其形成渊源、历史沿革、演变与发展规律、重大武术事件、重要武术人物、传承流派、拳种器械、技击功法及其文化精神、文化内涵、风格特点、价值观念、礼仪、道德规范等文化特质,这些特质综合起来,称为武当武术文化丛。武当武术是构成武当武术文化的实体和载体,脱离了武当武术,其文化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对武当武术文化丛的研究也可借助于1997年由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院校专业教材《武术理论基础》中所论述的“文化三层次说”进行分析,即“物器技术层”、“ 制度习俗层”、“ 心理价值层”三个层次。“物器技术层”是物质文化层面,它是武当武术文化形态的表面结构,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技术、器械、练功器具、场馆、服装等内容;“制度习俗层”是相对隐形的中间层,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的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教授方式、礼仪规范、武德的内容、比赛方式等内涵。“心理价值层”是最内层或最深层的武术文化形态结构层,它主要包括武当武术文化形态所反映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内容〔6〕。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与道教的发展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并在其道家理念和道教教义的特殊要求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技术理论体系,从某种角度讲,道家思想是武当武术的哲学基础及理论渊源。武当武术就是在守内、崇实、尚礼、自娱、修性、保身的理论观念指导下,运用太极说、阴阳说、五行说、八卦说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武当武术拳理、拳技、原则和战略。应该说武当武术的理论渊源是多元的,它吸收了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主,包含了传统医学、诸兵法内核,形成了对武当武术的多种学说理论和见解。
篇5
湿地油画地域文化地域差异
作为黑龙江人文地理资源的一个体现,湿地文化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湿地自然风景的表现具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存在着与其他地区文化特征的差异性。中国美术史上早已存在南、北方画派的画风文脉区别。无疑,所谓的“地域性”和“差异性”都不是浅层面的一些表象,还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需求。笔者力求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探讨黑龙江湿地作为地域特色文化,在油画表现中呈现出的面貌与南方湿地风景在油画表现风格中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
湿地一般分五大类: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黑龙江省的沼泽湿地是我国沼泽湿地分布最集中、最广泛的地区之一。扎龙湿地是我国北方同纬度地区中保留最完整、最开阔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天然的物种库和基因库,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以芦苇湿地广泛分布最具特色。可以说,以黑龙江扎龙芦苇湿地作为典型元素,研究黑龙江地域特色的湿地风景油画创作具有现实意义。
研究黑龙江地域特色的湿地风景油画创作首先要理清湿地的色调对我们的视觉的影响,以及自然景物承载的光与色彩的地域性文化差别。
一、季节性的色彩变化
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景物的固有色,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变化。黑龙江省的沼泽湿地,属于寒温带季风气候,霜冻期较长。因此,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颜色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呈现出季节分明的色彩变化。春季和夏季黑龙江芦苇沼泽湿地整体颜色呈由浅到深的不同绿色,而秋季和冬季湿地颜色呈现出从黄绿色到土黄色的不同变化。在霜冻期,由于冰雪覆盖,整个湖区呈现银白色,这是与南方湿地终年存在绿色的最大不同。那么,根据黑龙江扎龙湿地整体存在的固有颜色的变化,创作者可以确定表现芦苇沼泽湿地风景的油画基本用色,分为绿色调和黄色调以及白色调等,是具象油画表现色彩的基本色调。
二、亮丽的色调
除了考虑景物固有的颜色,在绘画中创作者还要思考光源色对画面的影响,不断丰富其光色的变化内容,不仅使画面本身的色调和谐自然具有层次感,还能使单调的色形呈现出空间体积感,增强了画面的可塑性及欣赏性。
我们都知道,日出、日落方向的天空是红色的,就连被它照亮的云层底部和边缘也变成红色了。原因在于空气的分子、水汽和杂质,使得光线的短波部分大量散射,而红色、橙色的长波部分,却散射得不多,那么就不难理解光线在水里面会折射。由于无数个水珠存在,光线就要折射无数次,光线在折射过程中是有损耗的。就南北方的空气湿度来分析,南方湿度大,空气中水分子含量高,太阳光到达地面时会受到水分子的折射,所以南方的天气经常会给人烟雨蒙蒙的感觉,这也是南方的特色。在常人眼中这种微小的变化几乎没有区分,但在画家挑剔而又敏锐的观察中就不可能无动于衷,南方风景画家早已把这种朦胧含蓄之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世人交流了,并形成了整体的风格。已故绘画大师吴冠中是江浙人,不仅从色彩上表现江浙一带的风景特色,同时又在中国画当中吸取了许多抽象元素运用于油画当中,为我们中西文化融合拓展了思路,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广西画家张冬峰所表现的风景画,色彩细腻而甜美,温润之感沁人心脾,这就是南方画家所捕捉到的南方水乡景色的魅力。而北方则不然,气候干燥,光线感强烈,景色更像叙事诗一般的壮丽,以感情的豪迈气魄而动人心目。北方的色彩明快,对比强烈,优美简洁概括,别具视觉冲击力,呈现亮丽的色调,也是笔者所强调的黑龙江省与南方各省市地区地域性的光线上的差别。
三、蓝色的和谐
环境色是物体表面受到光照后,除吸收一定的光外,也能反射到周围的物体上。环境色的存在和变化,加强了画面相互之间的色彩呼应和联系,能够微妙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作为黑龙江湿地元素之一的扎龙芦苇沼泽湿地,地处黑龙江省西部的松嫩平原。从表现内容上有蓝天、白云、芦苇、各种水鸟、冰雪,还有季节变化所赋予的颜色等,虽然没有南方景色山水相依的婀娜多姿,但绝不会缺少坚毅、苍劲、豪迈的气魄。这里我们可以分析表现内容之间色彩的相互影响。天空作为必不可少的元素,其色彩对其他景物色彩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北方比南方各省区云量少,日照时数多,而且辐射强度大,用湛蓝形容北方的天空一点也不为过。而这种天空的颜色对芦苇湿地其他景物的色彩产生影响,也会带有蓝色的倾向,其他景物的色彩必然与天空的颜色相呼应,形成整体的色彩和谐,而不是孤立的色块存在。由于平原地区物象相互遮挡现象较少,光影关系直观、明确,表现内容时更应该注意色彩的层次性变化与分布。
通过以上分析与论述可知,扎龙芦苇沼泽湿地作为黑龙江湿地特有元素在油画表现中色彩的应用规律。首先,应抓住季节色彩的变化规律,以及自然光色的特点,表现具有强烈色彩对比关系的画面效果。其次,以此为出发点表现以黑龙江湿地为特色的北方地域文化,以色彩的独特性表现南北方地域文化的差异。最后,色彩可以抽象为具体的地域文化符号,体现不同地区、地域的文化差异。黑龙江湿地风景油画表现的风格就可以体现这种色彩,使其抽象为具体的符号呈现给观众,使观看者体会到符号的象征意义——地域文化。
(注:本文为大庆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SK17)
参考文献:
[1]张亮.三江平原沼泽湿地岛状林植物区系特征及多样性分析.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 吴冠中.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艺术上海——76名家作品展》座谈会纪要[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