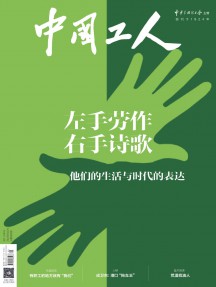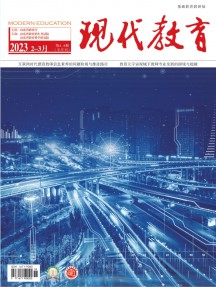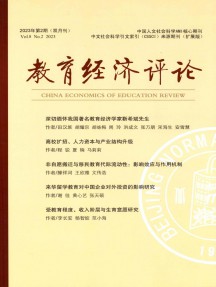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6:5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篇2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分割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不能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存在着流动性障碍。这种流动性障碍从市场角度来看,可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结果。具体来看,市场本身选择所形成的市场分割,实际上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由体制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复杂性。不论是哪种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其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力转换成本的存在,使企业在用外部人替代内部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越是企业的重要人才,劳动力替换成本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外部人”愿意接受比“内部人”更低的工资,但在低工资不足以弥补劳动力转换成本时,企业宁可用高工资雇用内部人,也不愿意用低工资雇用外部人。这样一来,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就成为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替换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必须为解聘员工而支付很高的解聘成本。解聘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比如支付给被解聘员工一定的费用、被解聘员工所留下的岗位一时招不进合适人选时所导致的损失等,也包括非经济成本,比如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等。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解聘成本是很高的。它们若想解聘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和干部(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高解聘成本,这其别是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巨大,前者比如被解聘员工的抵制和新闻媒介的报道等,后者比如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二是聘用新员工所必须支付的各种聘用成本,包括工资成本、搜寻费用、城市增容费和其他支出等。用人单位在替换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宁可继续在内部市场雇佣低素质的劳动力,也不愿意从外部市场中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
摘要:我国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市场分割情况,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造成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市场分割理论为分析和解决“知识失业”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篇4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